这是辛词中十分引人把稳的一首小词,构思新颖,构造奇特,措辞平浅又畅快,很能见出作者不拘一格的创造性。
上阕紧张发牢骚。或者说写忧郁的心情。
前两句就先交待自己的醉态,并表示醉得很畅快很爽,没有不愉快也没有工夫不愉快。如此强调,反倒坐实了词人之愁。醉中欢笑不过是现实太压抑的缘故。为什么现实感到窒息呢?
第三、四句词人便和盘托出。这两句化用的是《孟子》。他说他创造古人的圣贤书全是胡扯,都是骗人的。如此断交过分的话,正好暴露了词人巨大的痛楚。是那种现实跟空想之间重重障碍的抵牾把他卡住了的极度灰心。详细而言便是统一、规复的志向跟主和的冲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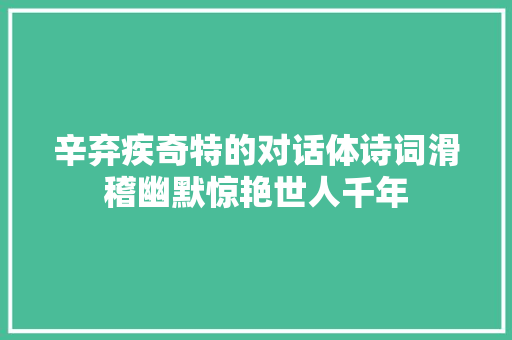
而后者常常占上风。辛弃疾本人也由于积极备战屡次被弹劾,终于到41岁彻底赋闲。一闲便是18年。也难怪他一时愤激,不信古人书。这里的四句都不好作字面意思解,由于都是气话、反话,是词人憋了一肚子火的发泄。
下阕词人展开了一次与“松”的互动。词风一改上阕的牢骚为诙谐有趣。
先是词人天真地问“松”,接着又把自己的乱晃算作是“松”要热心来扶,这时候词人像所有醉了却去世都不承认自己醉了的酒鬼一样,大声嚷嚷“我没醉!
我没醉!
”并一边把“松”推开。这一段可谓妙趣横生,刻画醉态入木三分。一个“去”字,既是倔强,又是洒脱,颇为真切。
这首别开生面的小令,最少有三个方面十分突出。
一,完备散文化笔法。如果说上阕还有些诗词的形式,下阕已经顾不得了,对话说来就来,诗词的节奏已然打乱,我说怎么写就怎么写,全无束缚,效果上很好地相符了二心坎的狂荡和多变。
二,将“松”拟人化,虚构与“松”的对话。这一段写得既有趣又表现词人的孤独。松、我即构成一个天下。词人通过醉的办法肃清了两者之间的措辞障碍,使这个不同平凡的天下也碰撞出精彩。
这种技法的利用在辛词中并不少见,像他那首也很特殊的《沁园春·杯汝来前》,便是通篇如此。这种写法在辛词中算是一绝。
三,全词只有一个意象:松。这在词里可谓罕见。哪怕只有二十字的绝句,每每也有三个以上意象,何况一首50多个字的词。连最常见的花、草、山、水、酒、风之类都没有。但读者却并不以为这首词缺少诗意。反而以为意韵十足。可见一首好诗并非离不开意象。
细读稼轩此调,当真别有滋味。作为词人一次任性的自由挥洒,此词并非没有问题。最大的毛病是上、下阕是分开的,彷佛并没有什么本色联系。上阕明显在发牢骚,到了下阕却进入另一个画风,两者并不在一个频率上。或许词人“遣兴”,本身只为随意抒发吧。
附词如下:
西江月·遣兴
醉里且贪欢笑,要愁那得工夫?比来始觉古人书,信著全无是处。
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