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想傻傻地问一声:有谁体会过去世了之后依然活着的滋味?
活在一泓泪水之湖波里,活在一围嗟叹的雾霭中,活在一片清梦的荒原上,永久地被所爱者的觉得所珍藏。至此,生者对付去世者的眷念,如灵魂的音乐、如上帝的措辞,贯穿生命。
这时,去世大概是残酷的,犹似乘一席白云、御两袖清风、洒脱而去,琴声般溶解于天空无尽的蔚蓝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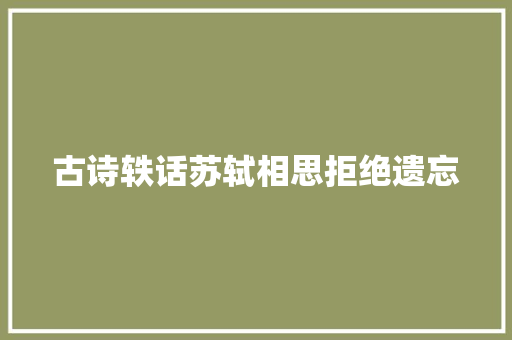
苏轼这首《江城子》彷佛在生与去世的界河上架起了一虹“上穷碧落下黄泉”的桥:
十年死活两茫茫,
不斟酌,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悲惨。
纵使相逢应不识,
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回籍,
小轩窗,正装扮。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断肠处,
明月夜,短松冈。
苏轼的这首词为吊唁结女亡妻王弗而作。
王弗16岁时嫁给苏轼,王弗脾气庄静娴柔,内秀于心。
起初苏轼不知其学识如何,读书时妻子王弗总是在身边默默地坐着,听着,苏轼偶尔忘了词儿,王弗就提醒,帮着背诵下来,甚或略加点拨而使茅塞顿开,苏轼甚是惊悦、心折。
当苏轼初涉仕途,年轻气盛,刚直不阿,每让平庸昏瞆的上司狼狈不堪,妻子王弗常劝勉苏轼既分歧流合污,又要谨言慎行,镇静处之。
家里来了客人,女人不能抛头露面,王弗从屏风后听到一些发言内容,已自有了评断。警觉苏轼:“那人巧语令色,机巧善辩,而又旁边逢圆,模棱两可,恐怕为人缺少诚挚。”
遇有顺情说好话、阿谀奉承者,更能看出可能热烈得快亦冷却得快,难成诤友……
很多事实证明了妻子王弗的判断,其远见卓识很使苏轼钦佩。
王弗也颇有诗的灵气。在随苏轼宦游颍州时,于一个月色清霁的正月之夜,见梅花怒放于庭前,不禁慨叹:“春月色胜于秋月色;秋月令人惨凄,春月令人和悦。何不邀几个朋友来,饮此花下。”
听了夫人的话,苏轼喜道:“我不知道夫人原来是位墨客,方才你讲的这番话,真是诗的措辞哪。”
于是,苏轼便邀来几位朋友,在梅花下饮酒赏月,并取夫人王弗的语意,即兴填写明晰《减字木兰花.秋月》:
春庭月午,摇荡春醪光欲舞。步转回廊,半落梅花婉娩喷鼻香。
轻云薄雾,总是少年行乐处。不似秋光,只与离人照断肠。
王弗在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病殁于开封,年仅27岁。
苏轼写此悼亡词时是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恰好10年之后,故有“十年死活两茫茫”之说。
死活相隔两不知,纵使强抑悲情,想要不去思念,又怎能忘怀?此时苏轼仕路坎坷,被贬于密州(山东诸城),与亡妻王弗安葬处四川彭山县相距千里之遥,以是说“千里孤坟”。亲人永别,自己一起风尘的酸楚、满腹牢骚的真言,也是“无处话悲惨。”纵或见面怕也难得认出,因我已满脸尘垢、两鬓霜染。
而真正的相逢,只能在梦中。
在梦中,忽而回到你我曾经朝夕相处的故乡,还和昔日一样,你临窗装扮。因要说的话太多,太多,无从提及,只有“相顾无言”。把千言万语倾注进感情含溶量最多的泪之流瀑……
料想着梦魂萦绕在那“断肠处”,你的坟地,清寒的月光笼罩植满青松的小小山岗。
那月光,是淡淡的往事,是浓浓的忧伤。
那月光,与泪水交融,流成楚楚动人的河,有一朵凄迷的小花,在水一方,如滚滚尘凡之外的一帧插曲,并非永久不能抵达的神往……
这悼亡词,不也是一条流着月光与泪光的河?
如果心是一叶比河更宽的船,那么,思念就比流水更悠远,比岸更长。
由于,相思谢绝遗忘。
真情,不属于去世亡!
#头条创作寻衅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