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魏曹植著《曹子建集十卷疑字音释一卷》
曹植才华横溢,传为他所作的《七步诗》妇孺皆知。六朝山水墨客谢灵运赞其“才高八斗”,无人可比:“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曹植《与杨德祖书》中“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一句亦引发诸多争议。曹丕《典论·论文》云:“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认为文章是可以辅佐政教统治天下的大事,应该推为历代不朽之奇迹。从字面看,曹植与其兄曹丕不雅观点相左,实际上,曹植所传达的仍旧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历代文人的根本代价不雅观,表示了意欲建功立业而不得的在野文人的无奈。曹丕、曹植所论并无抵牾之处,正是朝野不同态度的文民气坎天下的真实展现。
曹植墓石刻
《画赞序》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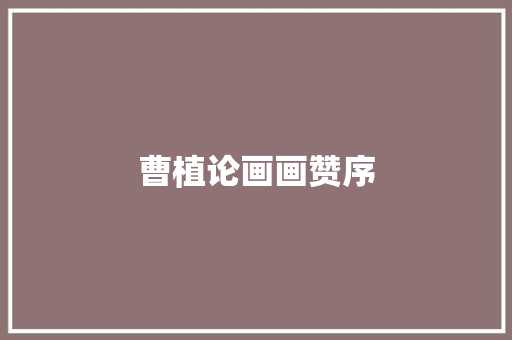
盖画者,鸟书之流也。昔明德马后美于色,厚于德,帝用嘉之。尝从不雅观画。过虞舜之像,见娥皇女英。帝指之戏后曰:“恨不得如此人为妃。”又前,见陶唐之像。后指尧曰:“嗟乎!群臣百僚,恨不得戴君如是。”帝顾而咨嗟焉。故夫画,所见多矣,上形太极混元之前,却列将来未萌之事。(《艺文类聚》卷七十四)
曹植以帝、后不雅观画之例喻绘画的功能。“画者,鸟书之流也。”这句话,阐明了绘画之起源,亦隐含了后世所云“字画同源”之意。他进而指出绘画的鉴戒功能之以是得以实现和倡扬,根本缘故原由在于绘画能有力地浸染于人们的感情:
不雅观画者,见三皇五帝,莫不仰戴;见三季暴主,莫不悲惋;见篡臣贼嗣,莫不切齿;见高节妙士,莫不忘食;见忠节去世难,莫不抗首;见放臣斥子,莫不嗟叹;见淫夫妒妇,莫不侧目;见令妃顺后,莫不嘉贵。是知存乎鉴戒者,图画也。(《全三国文》卷十七)
三国墨客曹植
曹植对情绪的重视是他诗文创作的一大特点,所作《洛神赋》即是描写黄初四年(223年)赴洛阳朝觐魏文帝曹丕的归途中,在洛水边重逢洛水女神宓妃,二人互传情愫,却无奈别离的爱情故事。凄美的哀情绝恋引发了历代文人墨客的创作欲望,以不同的办法传诵至今。《画赞序》丰富了以往绘画教养功能的内容,由于艺术能够以其独占的传染力潜移默化地浸染于人的情绪,绘画的教诲功能才得以历久的倡导和发展。曹植指出“不雅观画者”见“三皇五帝”、“三季暴主”、“篡臣贼嗣”、“高节妙士”、“忠节去世难”、“放臣斥子”、“淫夫妒妇”、“令妃顺后”,莫不产生“仰戴”、“悲惋”、“切齿”、“忘食”、“抗首”、“嗟叹”、“侧目”、“嘉贵”平分歧的感情,第一次将绘画的表现与不雅观者情绪密切联系,点明了绘画的“存乎鉴戒”绝非直接的说理教训,而因此“情”动人。
明 祝允明草书手卷曹植诗四首
序文终极归纳:“是知存乎鉴戒者,图画也,”承续了儒家政教不雅观点,是范例的绘画教诲功能的表示,这一不雅观点是对绘画发展初期紧张功能的总结,并不是曹植的独创,然而曹植挖掘出绘画之以是能够实现其教养功能的根本缘故原由——即对不雅观画者情绪的浸染,是值得我们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