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儿立志在苍生
1901年,邓恩铭出生于贵州省荔波县一个较为偏僻的水族寨子——水浦村落板本寨,邓家祖孙三代八口蜗居在三间茅草房,也只有二亩农田,生活极其贫乏。1905年,为了生存,同时为了躲避乡间匪患,邓家移居荔波县城生活,父母费力劳作,也仅能坚持最基本的生活。
年少的邓恩铭感想熏染到生活的艰辛,再加上目睹了诸多社会不平的景象,从小就跟奶奶学了不少反响水族贫民劳苦生活山歌的邓恩铭也学会了自己创作歌谣,寄寓邓恩铭对庶民苍生的深深同情,邓恩铭曾写过这样一首民谣:“种田之人吃不饱,纺纱之人穿不好;坐轿之人唱高调,抬轿之人满地跑。”歌谣用了比拟的手腕表现了现实生活的强烈反差,真正劳作的人其劳动果实总是被他人盗取,自己反而常常处于饥寒交迫的状态,这是一个多么不平等的社会啊!
诗歌字里行间渗透着邓恩铭对阴郁现实的强烈不满与对底层公民的同情怜悯。诗歌承继了古代歌谣“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邓恩铭激情亲切歌颂了清代荔波本地水族的叛逆师首领潘新简,所作《潘简王》诗曰:“潘王新简该当称,水有源头树有根。总为清廷政腐败,英雄叛逆救民生。”这是一首咏史诗,显然邓恩铭的创作具有借咏史以咏怀的意味,寄托了自己也要做一位“救民生”的英雄。正是由于对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贫苦百姓的恻隐与哀怜,邓恩铭青少年时候就萌发了大济苍生的救世抱负,他17岁离开故里除了为了升学之外,也是为了实现自己济世安民的空想。临行前所作《述志》一诗充分抒发了这一高远的情怀,诗曰:“南雁北飞,去不思归?志在苍生,不顾安危。生不敷惜,去世不敷悲。头颅热血,不朽永垂。”诗歌将自己形象地比喻成一只即将北行的大雁,虽有留恋故里之思,但为了社稷苍生,舍生忘去世,在所不惜。此诗为四言诗,直吐肚量胸襟,节奏明快,年夜方之气,贯穿全诗。如此肚量胸襟天下、志在苍生的人心理想在邓恩铭离去家乡时所写的其余一首咏怀诗《出息》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现,诗曰:“赤日炎炎辞荔城,出息茫茫事无分。男儿立下钢铁志,国计民生焕然新。”诗歌虽然写到了对个人出息命运难以预卜的茫然,但这更加武断了自己以改造国计民生为民气抱负的钢铁志向。要知道,邓恩铭离开家乡时年仅17岁,这样的志向真可谓“少年苦处当拏云”。
为国为民朝夕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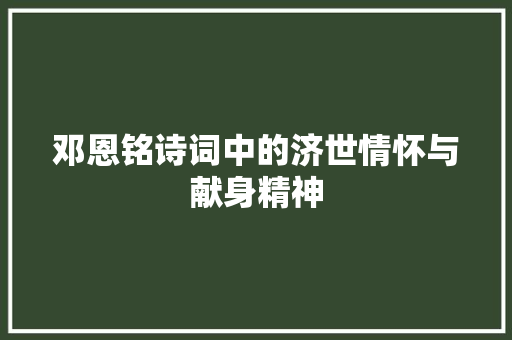
邓恩铭也是一位具有日常情性的人,他的书信尤其是给父母的书信也多次表达了对故乡的无限眷恋,流露了对父母的绵绵思念与不能尽孝于双亲膝前的愧疚之情。但为了救国救民的人心理想,他只能舍小家而忠于救国的大义。
邓恩铭离开家乡时写过一首《答友》的诗作,表现了革命奇迹如不堪利、誓不回籍的决心,诗曰:“君问归期未有期,乡关回顾甚依依。春雷一声震天地,捷报频传不我期。”诗歌既表现了乡关之思,更是抒发了天地换新颜之日才是自己的回籍之期,在怀乡与救国之间,邓恩铭首先选择的是救国,表现了自己要将生平奉献给革命奇迹的动人情怀。诚如其言,邓恩铭知行合一,他在1917年离开家乡后就没有再回过荔波故里,一贯忙于革命奇迹,直至生命的末了一刻,这何等令人感佩。他曾填过《江城子》这样一首词,词曰:“长期浪迹在他方,决心肠,不回籍。为国为民,永朝永夕忙。要把时潮流好转,大改造,指新航。年来偏易把情伤,披棘荆,犯星霜,履险如夷,不畏难常常。天地有时留我在,宣祖国,勃兴强。”词作表达了他为了国家和民族要不舍昼夜、忘我地事情,要将自己全部的生命奉献给祖国,奉献给天下百姓,无论困难与险阻,只是希望天地换新颜。邓恩铭来齐鲁大地之前曾咏叹古诗“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业不成誓不还。埋骨何须故里地,人间到处是青山”以抒怀,豪迈而劲放。当然对邓恩铭而言,他人生的奇迹不仅仅是学业,更是救亡图存的大我奇迹,反响了邓恩铭志在四方、“以国为家”的高尚情操。《江城子》和这首诗作相互照映,恰好印证了他为了革命奇迹奉献终生的博大情怀。
为国捐躯殇是福
真正的革命者为了伟大的共产主义奇迹总是能够将死活置之不理,邓恩铭同样如此,他曾经写过《决心》这样一首咏怀诗,诗歌作于邓恩铭192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中共一大的胜利召开鼓舞了邓恩铭,邓恩铭心潮澎湃,作诗以明志,表现了献身共产主义奇迹的决心。诗题语意显豁,诗作既直抒胸臆,又蕴藉蕴藉。诗曰:“读书济世闻鸡舞,革命决心放胆尝。为国捐躯殇是福,在山樗栎寿嫌长。”这首诗歌每句都利用了典故,藉典咏怀。“读书济世闻鸡舞”一句用了东晋祖逖与刘琨闻鸡起舞、相互勉励的历史典故,表明了自己要及时奋发、志在济世的决心。“革命决心放胆尝”一句则用了春秋时期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志在复国的历史典故,表明自己要哑忍雕励、志在救国的决心。“为国捐躯殇是福”又用了屈原《国殇》的文学典故,《国殇》一诗颂扬了将士们奋勇争先、雪洗国耻而为国捐躯的悲壮而崇高的精神,个体生命的非正常消亡本身是令人悲哀的事情,但在邓恩铭看来,为救国救民而献出年轻的生命是人生非常幸福的奇迹,彰显了其高亢的革命情怀,诗句丝毫没有流露出半点的悲哀之气。“在山樗栎寿嫌长”则用了《庄子》的文学典故,樗树与栎树因“大而无用”,故“不夭斤斧”之害,活得长久。在道家看来,此“不材之木”因“无为”而能达到逍遥游的境界,但于邓恩铭而言,这样的树木既然是无用之材,纵然能够存活一万年,实际上也是徒耗生命,毫无代价,在邓恩铭的笔下,它们成为了被讽刺鞭笞的工具。邓恩铭故意识地将此句与上一句关联在一起加以比拟,意在见告我们为革命、为国家奉献的生命才是真正故意义、有代价的生命。邓恩铭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此诗所表达的革命志向与奋斗情怀。
最令人冲动而敬仰的是邓恩铭的绝命诗《诀别》,此诗写于1931年,已经受了两年多监牢之灾的邓恩铭终极没有能够逃脱国民党的黑手,被枪杀于济南纬八路刑场。临刑前,邓恩铭年夜方悲歌,诗曰:“卅一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不惜唯我身先去世,后继频频慰地府。”邓恩铭捐躯时年仅31岁,这个“转瞬间”的年华可谓非常短暂,然而邓恩铭嗟叹的并不是人生的苦短,而悲愤的是这“救国救民”的壮志在有生之年他看不到实现的机会了,邓恩铭难以抑制内心的沉痛,只有悲愤地呵天发问。当然,墨客在悲愤之中又满含期待与希冀,自己虽然“出师未捷身先去世”,然而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捐躯能够唤起后来者连续为革命披荆斩棘,能够以不断的胜利告慰自己在地府之下的亡灵。这首诗歌很自然地让我们想到了陈毅《梅岭三章》中所表现的壮烈情怀,尤其是“后去世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大义凛然、前赴后继的革命精神是这两首诗歌在思想内容上的相通之处。邓恩铭面对去世神,无所畏惧,大义凛然,为了共产主义的奇迹流尽了末了一滴血,奉献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诗歌中所表现的墨客高大形象,可与日月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