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不见
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回!
《游玄都不雅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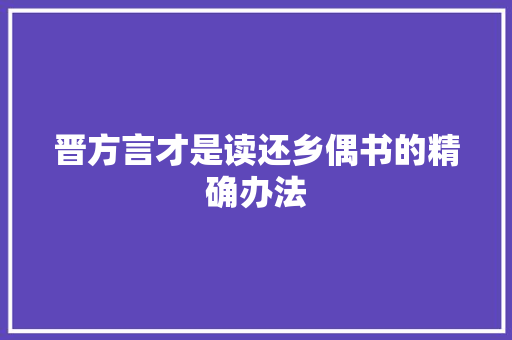
紫陌尘凡拂面来,
无人不道看花回(hui);
玄都不雅观里桃千树,
尽是刘郎去后栽(zai)!
李白《将进酒》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诗仙李白的名句传唱千古。但稍稍把稳一下,我们会创造这两句诗竟然不押韵!
同样的例子多不胜举。比如刘禹锡的《游玄都不雅观》:
紫陌尘凡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hui);
玄都不雅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zai)!
精美的古诗,读来不押韵,非常刺耳、令人难熬痛苦,让人以为好不怪哉。
严重的问题在于,小学老师这么念,中学西席这么读,大学教授依然这么教!
质言之,这不是误人子弟吗?
还有更为极度的例子。
幼年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贺知章的绝句《还乡偶书》,传唱千古,随处颂扬。但许多人就字面来理解,望文生义,首先把意思读偏了。
“儿童相见不相识”,儿童见了幼年离家老大方才归来的老者,自然不相识。这何足为怪,值得写诗一首吗?况且,儿童见了陌生人,特殊是官居极品的贺知章,会大方从容“笑问客从何处来”吗?再说,儿童既是乍见陌生人,状写这种情形也不宜用“相见”一词。因而,非常可能是墨客的儿时玩伴童年相识,此时已然老眼昏花,加之年头久远,相见时分认不出老大回籍的故人了。因而,人间沧桑,墨客才在平淡如一幅风尚画的绝句中,模糊透露出一位老年宦游人的独特感慨。
但更大的缺点是音韵方面的。为了押韵,或者是为了学术的严谨,乡音无改鬓毛衰的“衰”字,教授学者历来论证,该当别读为“摧”。以摧来解衰,意为摧折、疏落,未尝不可;但照顾了前两句的韵脚,结末第四句反而跑了韵。短短一首绝句,读来不押韵,不污染耳朵吗?
实在,按照古音韵,“回”该当读作(huai)。与下句的鬓毛衰(shui)是合韵的。如果教授固执,衰字在这儿非要以摧字来解读,也可以。那么,这时的摧字就也应该按古音读为(cuai)。这样,整首绝句读来顺口,听来也悦耳多了。
想那大唐之前的中华王朝,多数建都长安;我们山西(亦即河东)历来是京都的粮仓,人文荟萃,英才辈出。当时的京腔官话多数揉合了大量的晋陕一带方言古韵,而不类现在的京电影。山西地域封闭,交通不便,方言土语极少变革;正好因此,我们晋方言方才如活化石般保存着许多汉措辞的古来音韵。
我们可以假设,让一位初通笔墨的山西晋中平遥人来念《还乡偶书》,音韵方面绝对不会有什么问题。仅就读这首诗来评判,他天然地要频年夜学教授要高明不知多少倍。
当然,诗歌音韵千百年流变,一些字眼怕也是“幼年离家”,普通人、中小学生、包括教授们,平凡与之相见却也已是不相识了哩!
──几年前,我最初揭橥这点想法,有一位听说也是教授的师长西席提出不同见地。该师长西席认为,读古诗该当用普通话;由于一些字的古音究竟是怎么样的,谁也说不清。讲古典诗词的教授,不肯下功夫研究古音韵,又不肯从丰硕的方言资源中汲取营养,盘踞讲坛却误人子弟,叫人怎么称颂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