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纭。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赏析 在唐人赠别诗篇中,那些凄清缠绵、低徊留连的作品,固然动听至深,但其余一种年夜方悲歌、出自肺腑的诗作,却又以它的诚挚情意,倔强信念,为灞桥柳色与渭城风雨涂上了另一种豪放健美的色彩。高适的《别董大》便是后一种风格的佳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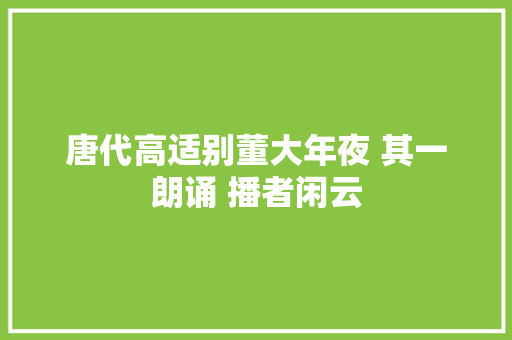
这首送别诗作于公元747年(天宝六年),当时高适在睢阳,送别的工具是著名的琴师董庭兰。盛唐时盛行胡乐,能欣赏七弦琴这类古乐的人不多。崔珏有诗道:“七条弦上五音寒,此艺知音自古难。惟有河南房次律,始终怜得董庭兰。”这时高适也很不得志,到处浪游,常处于贫贱的境遇之中。但在这两首送别诗中,高适却以爽朗的胸襟,豪迈的语调把临别赠言说得冲动大方年夜方,鼓舞民气。
从诗的内容来看,这篇作品当是写高适与董大久别相逢,经由短暂的聚会往后,又各奔他方的赠别之作。而且,两个人都处在困顿不达的境遇之中,贫贱相交自有深奥深厚的感慨。该诗写别离而一扫缠绵忧怨的老调,雄壮豪迈,堪与王勃“海内存心腹,天涯若比邻”的情境相媲美。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纭”。开头两句,描述送别时候的自然景致。黄云蔽天,绵延千里,日色只剩下一点余光。夜幕降临往后,又刮起了北风,大风呼啸。伴随着纷纭扫扬的雪花。一群征雁疾速地从空中掠过,往南方飞去。这两句所展现的境界阔远渺茫,是范例的北国雪天风光。“千里”,有的本子作“十里”,虽是一字之差,境界却相差甚远。北方的冬天,绿色植物凋零殆尽,残枝朽干已不敷以遮目,以是视界很广,可目极千里。说“黄云”,亦极范例。那是阴云凝聚之状,是阴天景象,有了这两个字,下文的“白日曛”、“北风”,“雪纷纭”,便有了着落。如此理解,开头两句便见出作者并非轻率落笔,而是在经由了苦心酝酿之后,才自然流一出的诗歌措辞。这两句,描写景物虽然比较客不雅观,但也处处显示着送别的情调,以及墨客的气质心胸。日暮天寒,本来就随意马虎引发人们的愁苦心绪,而眼下,墨客正在送别董大,其执手留恋之态,我们是可以想见的。以是,首二句只管境界阔远渺茫,实在不无凄苦寒凉;但是,高适毕竟具有恢弘的气度,超然的禀赋,他开没有沉溺在离去的感伤之中不能自拔。他能以理驭情,另具一副心胸,写出年夜方冲动大方的壮伟之音。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这两句,是对董大的抚慰。说“莫愁”,说前路有心腹,说天下大家识君,以此赠别,足以鼓舞民气,勉励人之心志。听说,董大曾以高妙的琴艺受知于宰相房琯,崔珏曾写诗咏叹说:“七条弦上五音寒,此艺知音自古难。惟有河南房次律,始终怜得董庭兰”。这写的不过是董大遇合一位知音,而且是官高位显,诗境难免不免狭小。高适这两句,不仅紧扣董大为名琴师,天下外扬的特定身份,而且把人生心腹无贫贱,天涯处处有朋友的意思融注个中,诗境远比崔珏那几句阔远得多,也深厚得多。崔诗只是琴师出生的材料,而高诗却堪称艺术珍品。
墨客在即将分离之际,全然不写千丝万缕的离愁别绪,而是满怀激情地鼓励朋侪踏上征途,欢迎未来。诗之以是卓绝,是由于高适“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殷璠《河岳英灵集》)、“以气质自高”(《唐诗纪事》),因而能为志士增色,为游子拭泪。如果不是墨客内心的郁积喷薄而出,则不能把临别赠语说得如此谅解入微,如此武断不移,也就不能使此朴素无华之措辞,铸造出这等冰清玉洁、醇厚动人的诗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