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迅在教室辅导学生的情景)
校长写书,写什么?观点化?体系化?怎么观点化?怎么体系化?从实践上升到理性,怎么上升?办法呢?路子呢?我是李迅的校长班同学,那是2009年,我国正高下同等呼唤教诲家,培养教诲家的年代。我与李迅成为教诲部校长培训中央首期全国精良中学校长高等研究班的同学,集中培训与分散在各自学校实践相结合,韶光跨度三年。从此,我们便是“终生的同学”,纵然卒业往后,我们险些每天联系,开始是短信,后来是微信,我可以说,是理解他的人,理解他的办学,以及他的学校;理解他的生活,乃至与他父母、家人都有过互换;理解他的爱好,他的一些朋友,男女老少,他都故意无意先容我认识。但是,本日我坐下来翻开他的《俯仰》,彷佛统统变得模糊起来、朦胧起来,才知道,我对他竟然还不是真正地理解。
李迅校长彷佛是靠着自己的聪颖与勤奋,一起脱颖而出。从村落庄中学,到县中,到福州一中,从老师到教务主任,到校长,从学科到管理。32岁即被评为数学特级西席,然后连续两年辅导、辅导学生得到数学奥林匹克国际赛冠军。险些所有的名誉都拿到了。全国前辈西席、劳动模范、国务院津贴,乃至还竟然入选为中宣部“文化名家‘四个一批’人才”、入选国家“万人操持”,教诲内部的名誉获奖项拿拿也罢了,还能走出教诲去拿。不过,我却常常取笑他,在我们校长研究班,是少数几个没有被研究“教诲思想”、被举行教诲思想研讨会的人。
这是一件有趣的事。我常常为他打抱不平,去有关老师面前去“嘀咕”。我们的副班主任王俭老师是一个常常有灵光闪现的人,他常把“吾师”与“真理”放在同等位置,很可爱,也便是要我们像爱真理一样爱他。与我是同乡,我什么话都敢与他说,我发牢骚,他两手一摊,显得无可奈何的样子。我在乎,李迅不在乎。他知道了,总是说,柳兄,你干啥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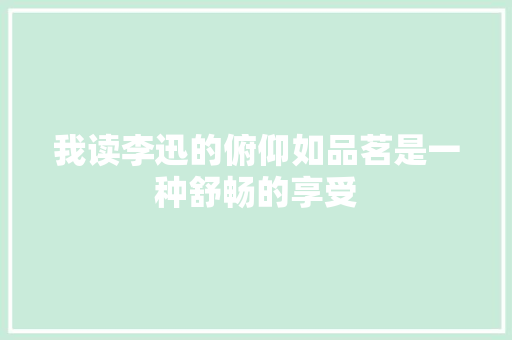
我曾读他的《从游》,那是他的教诲随笔集,是我认识他之后,读到的第一本教诲随笔,之前他写了不少关于数学的书,《从游》这本书,是他交的作业,校长研究班每人须要梳理自己的教诲实践,从而上升到理论层面,然后把不清晰的东西凸显清晰,把零星的串成系统。李迅大概就交了这本书为作业。这怎么行呢?一件件事、一个个小故事,仍旧是零星的、不成体系的,没有光鲜地提炼出能概括自己教诲思想的观点。自然过不了关。不过,我却认为这本书挺好,出版后,我负责阅读,写了一段笔墨发在微信朋友圈里,我说:
“本书是福州一中李迅所著,他曾是我校长班同学。多年来我们险些每天联系,没想到一个数学老师,写下本属于我们语文语文老师的笔墨。所有的篇章都都翻了一下。琳琅满目,有山水河流,有野花野草。有教诲,有传授教化,有心灵的独语,有对世俗的嘲讽,有朋友间的密语,有像站在街头的叫嚣。有数学,有语文,有散文诗,有诗词,有教诲的感悟。我最喜好的还是斯托夫人,是马克吐温,那些篇章中有体温,有内心的渴望与眷恋。文集最名贵之处,还是心中有学生,有与孩子们心与心的互换,并渗透自己对教诲的,对传授教化的,对数学教诲传授教化的理解。一边品着新茶,一边读他的文章。那也是乐趣,也是享受。”
由李迅,触发了我的思考。本日,手拿这本《俯仰》,更是感慨。感慨是多方面的,不能自已。我觉得有些不公,我平时写的笔墨,有关教诲的,有关行走读书的诗文,每每会发给他看。然而,他写了这么多,险些每天写,我却浑然不知,直到书放在我的书案上。想想,生一下气,罢了,谁叫他是数学老师呢?精通数学的人,或许都是多一个心眼的人。这本书,还真是可以负责阅读的书。共有六辑,六个方面,涉及到学校教诲、学科追求、人生意见意义,从校内到校外,海内到国外,从老师到学生,从日常教室传授教化到国际奥林匹克竞赛场面。没有空泛的大道理,更没有说教,生活中点点滴滴,在贰心里都能荡起荡漾,网络在笔下。
(福州一中承办了全国第三届中学生校园诗会,诗会上李校长与我一起回答小提问。)
比如《且辩且行,无缘大悲》,写的便是一次我们在短信、微信上“吵架”的故事。我说了一句:我们要培养未来的李敏华(校友、中科院院士)、院士。引发他对我的“鞭笞”,说:培养未来的李敏华,就够了,为何还要加上“院士”二字?我公开拓在微信圈里,引发了许多人的谈论、辩论,然后,我们各自思虑之后,我立时写出了笔墨,再发他。他也写了,不过,却没有见告我,直到出书,我才瞥见,细微之处,可见我们不一样。然而,也窥见他的教诲境界确实不一般。
《俯仰》这本书,于我而言,很亲切,他所写的一些事情,我知道,或者我也在场。全国中学生诗会,他是发起者之一,积极倡导,不遗余力,第三届在福州一中举行。他约请来了台湾墨客郑愁予、毛杰(现为河南省教诲厅副厅长)约请来了中心电视台新闻主播海霞,隆重而神圣。当时为了办诗会,清华大学正举办的全国百所名校长论坛,邀李迅校长作主旨演讲,被他回绝,派副校长参加,清华大学竟没有生气,仍付与他们学校“最佳发展奖”以表彰福州一中学生在清华学习期间的表现。何重何轻?贰心中自分量。诗会,是我们语文老师的事情,他是组织者,我以为他只是行政支持,看了本书之后,他真是深入个中。一天的诗会,他却连续写了三篇文章:《天真至性出诗肠——致‘海峡听潮’第三届全国中学生校园诗会》、《彩虹色显不出梦幻——‘海峡听潮’第三届校园诗会随感》、《生命中总有一条路适宜自己——‘海峡听潮’第三届全国中学生校园诗会随感》。他说:
“《海峡听潮——第三届全国中学生校园诗会作品选》中的日间与黑夜,溪流与海洋,落叶与流萤,自由与背叛······彷佛都像野外上的小花,多彩,并不柔弱;是蓝天中鸣叫的鸟儿,婉转,并不矫揉;是内心里流淌的泉水,清亮见底,并不肤浅;如雨后的天空,统统都是那样的清新、亮丽,又韵味深长······”
一个数学背景的校长,如此抒怀、如此多情,真的是难能名贵。这本书,与其是一本教诲随笔,不如说是一个校长的日记。现在书的体例是按专题排列的,韶光交叉,如果按韶光排列,一个校长每天的所做、所想、所思,就会清晰地如一座山蜿蜒,或如一条河流淌。这本书,与其说是一个校长的事情日记,不如说是一个校长的心灵旅程。许多的学校征象、教诲的征象,都会引发贰心灵的拷问、良知的拷问,如《灵魂永久站立着》、《我们缺的是什么》、《为何事情中总有遗憾》、《陪你‘追梦’的忧与乐》、《理从疑总来》、《教室惹的‘祸’》等等,俯拾皆是。
为什么苏霍姆林斯基能成为苏霍姆林斯基?由于苏氏在帕夫雷什中学,与之融为一体。在师生之间,形影相随,心更随之。他的著述,冲动我们的都是那些苏氏日常碰着的人与事,并授予它们教诲的意义。很少有宏篇大论式的理论阐述,苏氏的名贵在于鲜活的细节,在于以情动人,东风化雨,润物无声。
此刻,我突发奇想,如果苏氏参加了我们海内的旨在培养教诲家校长的“研究班、培训班”等工程,苏氏会是什么样子?他的《给西席的100条建议》、《我把心献给孩子》、《学生的精神天下》、《教诲的艺术》等著作,许一个个动听的教诲案例,还是现在这个样子吗?我想到了校长的自然生态问题,自然生态当然不等同于原始生态。所谓大器不雕与玉不雕不成器,这两者如何折衷?
我曾去贵阳应邀参加教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央举办的一个全国校长论坛。中央的领导、教授都在场,我说了我的不雅观点,我说:一个“好校长”是不说绝对的话的人、一个“好校长”是不做极度事情的人,乃至一个“好校长”是不时时处处事事争第一的人。凡事都不能绝对,我们过去太多的是绝对,说绝对的话,做绝对的事。我阅读了一些当下出版的教诲书,有的人喜好标新创新、哗众取宠;有的人像一个教诲的不雅观察员,站在高处,指示江山,叫别人该当这样做,不应该那样做;有的人随着社会舆情走,以此成景象、立山头。对照这本《俯仰》的平常、淡定、坚韧,写的都是冲动自己、冲动别人的教诲故事、案例、感悟,何不让人触动?李迅接管三年教诲家培训,彷佛并不看重“体系化”、“观点化”,是喜是忧?看问题的标准不一,很难说得清楚。不过,我为他叫好,这些散落在地上的珍珠,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是教诲俏丽的景致。论坛上,我说,或许“体系化”、“观点化”并不适应每一个校长。我竟然大胆地对老师发起了“寻衅”,王俭教授坐在那里对我微笑,他立时在我们校长班的同学群里说,柳校长向我“寻衅”了。然后接着加了一句“不敢寻衅老师的学生不是好学生”。中央主任代蕊华教授在论坛总结时还专门回应,对我的不雅观点表示了认同。论坛结束,中央副主任沈玉顺、刘莉莉教授等上来与我激情亲切握手。一阵惬意,让我心里暖暖的,老师究竟是老师,大气、豁达,何其好啊。
2021年10月10日修正
编后解释:
这是一篇旧作,再次刊登于此。李迅校长也早已从福州一中校长的岗位上,调到了福建省教诲厅副厅长的岗位上,主管根本教诲。近年来,福建的根本教诲频频有好招,我相信与李厅长分不开,他熟习根本教诲,贴近校长、老师、学生、家长。苏州的教诲同行,理解了福建的教诲情形后,屡次建议我写写李厅长,如何不先再发一下我的阅读体会呢?
(我们一起出访美国时的合影,第二排左二弯腰者为李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