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样平常来说,鲜花是女性化的,用女性来拟人化形容是非常恰当的。但大多数的鲜花都是妩媚的,绝不是素面朝天的女性来形容的,因此,传统文化中,最常利用美人妆来形容鲜花,而且是习认为常。
非常故意思的是,女性装扮随着韶光、场合的不同而不同;而鲜花呢?而又由于品种不同,各种鲜艳、妩媚也是不同的。墨客们便是捉住这样的特点,利用不同的装扮来形容不同的花儿品种,也形容同一种花儿的不同情景。
1. 半醉西施晕晓妆,天喷鼻香一夜染衣裳,傅察牡丹是传统文化中最富丽堂皇的花儿,人们形容牡丹,常日是用“四大美人”来相互比喻。比如,诗仙李白就用牡丹来形容杨玉环,“云想衣裳花想容”,这里的花儿,便是牡丹花。而这首宋代墨客傅察的《牡丹》,则是用另一个美人,西施来形容牡丹:
半醉西施晕晓妆,天喷鼻香一夜染衣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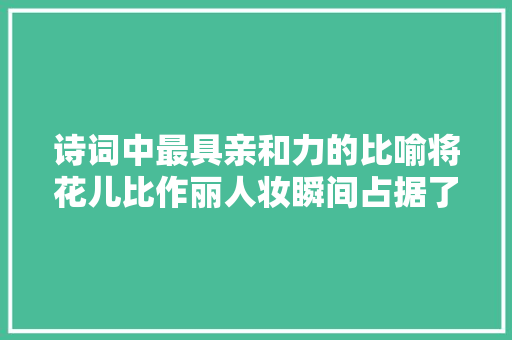
犹豫欲画无穷意,笔法何人继赵昌。
半醉西施晕晓妆,天喷鼻香一夜染衣裳
“半醉西施晕晓妆,天喷鼻香一夜染衣裳”,牡丹花开大红大紫,非得用美人醉酒后的红晕来形容才得当。以是,墨客用半醉的西施脸上的红晕来形容,但他以为还不足,一定是西施早上装扮过过,才能配得上牡丹的雍容华贵,素面的西施还不足。还不足,这个时候,西施穿的衣裳,一定是利用天喷鼻香刚刚在夜里染过的。
可以看出,在墨客眼中,一个素面的西施够不上牡丹的俏丽,必须得化过妆;而一个仅仅化过妆的西施仍旧不足,得是半醉的西施,得要那醉酒后脸上的红晕;但这仍旧不足,还配不上牡丹的喷鼻香气,得要西施穿的衣服,是上半夜刚刚用天喷鼻香熏了一夜的衣服,浑身散发出天喷鼻香才行。
这样的西施,才配得上牡丹的“国色天喷鼻香”!
这首宋代墨客苏泂的《荷花》,一反历朝历代墨客写荷花的老例,一样平常写荷花,都会描写它“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特点。但苏泂并未拘束于老例,而是描述出一个与老例不一样的荷花:
荷花宫样美人妆,荷叶临风翠作裳。
昨夜夜凉凉似水,羡渠宛在水中心。
荷花宫样美人妆,荷叶临风翠作裳
“荷花宫样美人妆,荷叶临风翠作裳”,墨客直抒胸臆,直接说荷花是“宫样美人妆”。作甚“宫样美人妆”,指的是皇宫里贵妇的装扮,一样平常是高高的发髻,高挑的身材,临风欲舞,这跟荷花非常的贴合。
墨客道出了荷花“宫样美人妆”的特点,一反传统文化中荷花那种“池上芙蕖净少情”的特点,说荷花的打扮是“宫样美人妆”,一点都不少情。
“羡渠宛在水中心”,更是说荷花是“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是可以追求的。它给人的间隔感,只是由于它“在水一方”而已,并不是“净少情”,而是像一个“宫样美人妆”的少女,值得我们去追求。
3. 学得汉宫妆,偷传半额黄,吕本中历来写黄花,比如,菊花,很少有真切的。个中如易安居士的“人比黄花瘦”,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了。一样平常都着重于写黄花的精神,比如,“宁肯枝头抱喷鼻香去世,何曾吹落北风中”。要说精神,腊梅的精神愈甚于菊花,由于腊梅更有凌霜傲雪的气势,非菊花能比。但吕本中就偏偏不写腊梅凌寒的精神,而是着重于它的俏丽:
学得汉宫妆,偷传半额黄。
不将供俗鼻,愈觉更暗香。
学得汉宫妆,偷传半额黄
“学得汉宫妆,偷传半额黄”,“汉宫妆”,看重两点,一是身材的苗条,二是装扮的颜色,已经盛行粉底、胭脂,是中国彩妆的开始。“额黄”,一种古时汉族妇女的美容妆饰,也称“鹅黄”、“鸦黄”、“约黄”、“贴黄”,“花黄” 。 因以黄色颜料染画或粘贴于额间而得名。
腊梅树已经学得了“汉宫妆”的精髓,它身材高挑,特殊是那盛开的腊梅花,就像盛妆美女额上的额黄,是那么的迷人。
“不将供俗鼻,愈觉更暗香”,这一句又赞赏了腊梅那凌霜傲雪的气质,它一样平常开在雪窖冰天里,一样平常不耐寒冷的俗人是不可能在雪窖冰天欣赏腊梅花的。以是,墨客说它不把喷鼻香气给庸俗之人来闻,只有不畏寒冷的志士才能欣赏到,而且是愈闻愈觉其暗香。
4. 转镜失落花处,方知不是妆,柳应芳这首明代墨客柳应芳的《咏美人梅花对镜》,写得很妙,他没有明写梅花像什么什么妆,而因此一个美女在真正扮装过程中发生的趣事,来刻画梅花那动人的美,和美人的妆真正是天衣无缝的:
晓起一开镜,梅花影镜傍。
转镜失落花处,方知不是妆。
转镜失落花处,方知不是妆
“晓起一开镜,梅花影镜傍”,美人早上一起来,就打开妆镜台,开始扮装,而这个时候,梅花适值开放在铜镜旁。
这首诗,一开头就交代了故事背景。
“转镜失落花处,方知不是妆”,短短十个字,却包含了一个起伏跌宕的故事:美人看到自己头上有一个梅花妆,很是奇怪,明明自己没化过梅花妆啊,哪里来的梅花妆呢?
正百思不得其解,她考试测验着迁徙改变铜镜,想看看梅花是怎么插到头上去的,没想到镜子一转,却头上没有了梅花,这才知道,这不是梅花妆,而是真正的梅花。
这首诗,以一个“是妆”还是“不是妆”的疑问,美人把梅花当成了自己头上的装扮,自然是由于梅花的俏丽,从而赞赏了梅花丽质天成的特点。
5. 馆娃人尽醉,西子始新妆,吴融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喜好的花儿,基本上以精神意境为主,这可能便是蔷薇在浩瀚“咏花”诗词中占比很少的缘故吧。“咏蔷薇”的诗词不但少,个中的佳构就更加少之又少。这首唐代墨客吴融的《蔷薇》,可以说是个中的佳构,没有之一:
万卉东风姿,繁花夏景长。
馆娃人尽醉,西子始新妆。
馆娃人尽醉,西子始新妆
“万卉东风姿,繁花夏景长”,冬去春来,日渐融和,万木复苏,一旦东风骤起,便逗得万卉争发,群芳吐艳。春花大都开在仲春和暮春时节,虽然争妍一时,但几番风雨便落英缤纷了,给人以繁华一时、瞬息即逝的觉得。夏天则不然,这个时令里不但着花的品种繁多,而且许多花的花期尤长。
蔷薇的花期长是它的一个特点。
“馆娃人尽醉,西子始新妆”,“馆娃”,春秋时吴王夫差为越国供献美女西施所建的馆娃宫。
当蔷薇开放时,就像西施刚刚换上新妆一样,让馆娃宫里所有的人都陶醉了。
一句,“西子始新妆”,高度赞赏了蔷薇的美,只有刚刚化完妆的西施可以媲美。我都知道,美女新妆有一种特殊让人惊艳的觉得。当她的这个妆扮久了,那么各种护肤品被氧化,效果就差远了;其余,一个妆扮让人看久了,也会腻了。
以是,“西子始新妆”,是对蔷薇最高的赞赏!
传统文化中的花儿,历来是年夜家站的角度不一样,意象也各不相同。比如“桃花”,唐代墨客崔护就把它形容成最完美的恋人,“人面桃花相映红”;而到了诗圣杜甫那里,却是“轻薄桃花逐水流”的水性杨花之流。但墨客们对付海棠,却是异口同声。大文豪苏轼写道,“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把海棠描写成一个俏丽嗜睡的女孩。宋代诗僧德洪则从另一个角度描写海棠的女性美:
酒入喷鼻香腮笑未知,小妆初罢醉儿痴。
一枝柳外墙头见,胜却千丛著雨时。
酒入喷鼻香腮笑未知,小妆初罢醉儿痴
“酒入喷鼻香腮笑未知,小妆初罢醉儿痴”,“未知”,指处于一种迷茫的感知状态。就像一个美女,刚刚喝下美酒,喷鼻香腮一片嫣红,似笑非笑,似嗔非嗔;她稍稍做了一下淡妆,有些醉了,目光痴痴的,似要睡去。
这就和苏东坡的“只恐夜深花睡去”对应上了,把海棠花有些慵
一句,“酒入喷鼻香腮笑未知,小妆初罢醉儿痴”,墨客认为用醉酒后的“腮红”来形容海棠红还不足,得加上“小妆初罢”。是女孩精心做了淡妆后,再醉酒后的“腮红”,才配得上海棠红。
值得把稳的是,由于海棠花娇小,以是,墨客用“小妆”来形容是非常恰当的!
明代墨客李东阳,描写玉簪花,那也是不吝溢美之词,那险些是把天上人间,所有的美好都给了玉簪花。他在《玉簪花》中写道:
昨夜花神出蕊宫,绿云袅袅不禁风。
妆成试照池边影,只恐搔头落水中。
妆成试照池边影,只恐搔头落水中
“昨夜花神出蕊宫”,“蕊宫”,在玄门经典中被称为仙宫,是神仙居住的地方。昨天夜晚,花神从神仙居住的仙宫出来。
第一句,便是将玉簪花比喻成花神,但在墨客眼里,这显然是不足的。
“妆成试照池边影”,就算是花神,也假如扮装之后,才够得上玉簪花的靓丽,玉簪花风采。
这还不足,“只恐搔头落水中”,花神扮装后的头饰中,一定要有一步一摇的搔头,才还配得上玉簪花的神韵!
就算把牡丹比喻成杨贵妃,就算把蔷薇比喻成西施,那里比得上把玉簪花比喻成花神更高一筹,更何况是妆成的花神。
8. 晓妆如玉暮如霞,浓淡分秋染此花,刘子寰提及将花儿比喻成美女的妆扮,这首宋代墨客刘子寰的《芙蓉花》,则是更上一层楼。别人家比喻妆扮,要么是盛饰,要么是淡妆,要么是晓妆,要么是晚妆,再要么是新妆。总之,是一种妆扮。而这首《芙蓉花》,则是同一种花儿,有两种妆扮:
晓妆如玉暮如霞,浓淡分秋染此花。
终日独醒干底事,晚知烂醉是生涯。
晓妆如玉
暮如霞
“晓妆如玉暮如霞”,芙蓉花是一个百变精灵。它早上是晓妆,如玉一样洁白,一样温润;而旁晚则是晚妆,顿时残酷如彤霞。
这是更加拟人化的描写,由于只有人才知道早妆和晚妆的不同,这更加展现了芙蓉花的灵性。
而这一句,“终日独醒干底事,晚知烂醉是生涯”,进一步阐述了它的灵性。为什么要整天保持一个如玉一样温润而复苏呢?这样不是很累吗?何不到了晚上,喝过烂醉,让面庞像彤霞一样嫣红,这才是人生。
一句,“晓妆如玉暮如霞”,准确的捉住了芙蓉花的特点,花儿的美,跟女孩的美一样,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妆扮,有不同的俏丽,这才是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