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三卷本诗选的译者汪飞白师长西席完备没有这个条件。他连轻微整块一点的韶光都没有。五十岁前翻译这些诗歌时,他还是一名军人。读这套译诗集的后记,也很故意思。汪师长西席在文末注着这样两行字:
1979年10月记于白云山麓部队驻地
1981年9月校改于杭州大学。
汪师长西席是1980年辞去军职转入杭州大学中文系专事教书和翻译的。而我们刚好也是这一年的新生。当时我们只知道汪老师曾是一名军官,却不知道是什么职务。最近读了《浙江作家》里对汪老师的访问记,才知道他离开军队时,是某驻广州部队的政委,而且在长期的军旅生涯中,他都是一名军队政工干部。他常常下部队,事情是非常紧张的。那么他是怎么译诗的呢?访问记的作者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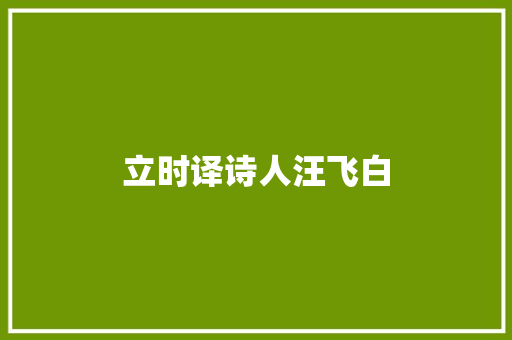
原来他是利用乘车韶光从事诗歌翻译的。他译诗的常规是:每天早上出发前看一眼原文诗,常日就记住两三小节,然后在军用吉普车上心中默译。他就这样日积月累,译出了一部又一部诗歌名著。
本日我在他为《马雅可夫斯基诗选》所作的后记中,也读到类似的阐述:
由于军务繁忙,业余韶光是根本谈不上的。我译诗的韶光紧张来自下部队途中和等待开会的韶光。正如马雅可夫斯基在《登上旅途》中描写的那样,车辆的颠簸化成了诗的节奏:
磕,碰,
磕,碰,
诗在舞蹈。
磕,碰,
磕,碰,
韵律在敲。
如果把马雅可夫斯基和汪飞白师长西席乘坐的车,回到古代复原成骏马的话,马雅可夫斯基就可以被称作“马背墨客”,而我们的汪老师,自然便是“马背译墨客”了。
所谓“非常之人,方成非常之事”,或者说,建不世之功者,必是保持不懈之士。我们的汪老师正是这样的非常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