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读书
十几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短文谈读书,这问题实在是谈不尽,而且这些年来我的见地也有些变迁,现在再就这问题谈一回,趁便把上次谈学问有未尽的话略加补充。
读书并不在多,最主要的是选得精,读得彻底。与其读十部无关轻重的书,不如以读十部书的韶光和精力去读一部真正值得读的书;与其十部书都只能泛览一遍,不如取一部书精读十遍。
“好书不厌百回读,熟读寻思子自知”,这两句诗值得每个读书人悬为座右铭。读书原为自己受用,多读不能算是名誉,少读也不能算是耻辱。少读如果彻底,必能养成寻思熟虑的习气,涵泳优游,以至于变革气质;多读而不求甚解,则如驰骋十里洋场,虽珍奇满目,徒惹得心花意乱,空手而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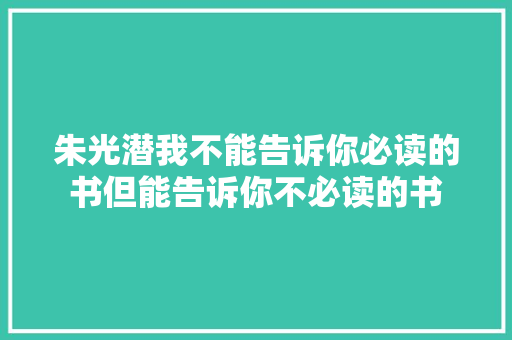
有些人读书,全凭自己的兴趣。本日碰着一部有趣的书就把预拟做的事丢开,用全副精力去读它;来日诰日碰着另一部有趣的书,仍是如此办,虽然这两书在性子上绝不干系。一年之中可以时而习天文,时而研究蜜蜂,时而读莎士比亚。在旁人认为主要而自己不感兴味的书都一概置之不理。
这种读法有如打游击,亦如蜜蜂采蜜。它的好处在使读书成为乐事,对付一时兴到的著作可以深入,久而久之,可以养成一种不平凡的思路与胸襟。它的坏处在使读者泛滥而无所归宿,缺少专门研究所必需的“经院式”的系统演习,产生畸形的发展,对付某一方面知识过于重视,对付另一方面知识可以很无知。
我的朋友中有专门读冷僻书本,对付正经正史从未干涉干与的,他在文学上虽有造就,但不能算是专门学者。如果一个人有韶光与精力许可他过享乐主义的生活,不把读书当做事情而只当做消遣,这种蜜蜂采蜜式的读书法原亦未尝不可采取。但是一个人如果抱有造诣一种学问的志愿,他就不能不有预定操持与系统。对付他,读书不仅是追求兴趣,尤其是一种演习,一种准备。有些有趣的书他须得捐躯,也有些初看很干燥的书他必须咬定牙关去硬啃,啃久了他自然还可以啃出滋味来。
读书必须有一个中央去坚持兴趣,或是科目,或是问题。以科目为中央时,就要精选那一科要籍,一部一部的从头读到尾,以求对付该科得到一个概括的理解,作进一步作博识研究的准备。读文学作品以作家为中央,读史学作品以时期为中央,也属于这一类。
以问题为中央时,心中先须有一个待研究的问题,然后采关于这问题的书本去读,用意在搜集材料和诸家对付这问题的见地,以供自己权衡去取,推求结论。主要的书仍须全看,别的的这里看一章,那里看一节,得到所要搜集的材料就可以丢手。
这是一样平常做研究事情者所常用的方法,对付初学不合适。不过初学者以科目为中央时,仍可大抵采纳以问题为中央的微意。一书作几遍看,每一遍只着重某一方面。
苏东坡与王郎书曾谈到这个方法:“少年为学者,每一书皆作数次读之。当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并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故愿学者每一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兴亡治乱圣贤浸染,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别作一次求业绩文物之类,亦如之。他皆仿此。若学成,八面受敌,与慕阅读者不可同日而语。”
朱子尝劝他的门人采取这个方法。它是精读的一个要诀,可以养成仔细剖析的习气。举看小说为例,第一次但求故事构造,第二次但把稳人物描写,第三次但求人物与故事的穿插,以至于对话、辞藻、社会背景、人生态度等等都可如此逐次研求。
读书要有中央,有中央才易有系统组织。比如看史籍,假定把稳的中央是教诲与政治的关系,则全书中所有关于这问题的史实都被这中央联系起来,自成一个别系。往后读其它书本如经子专集之类,自然也常遇着关于政教关系的事实与理论,它们也自然归到从前看史籍时所形成的那个系统了。一个人心里可以同时有许多系统中央,如一部字典有许多“部首”,每得一条新知识,就会依物以类聚的原则,汇归到它的性子附近的系统里去,就如拈新字贴进字典里去,是人旁的字都归到人部,是水旁的字都归到水部。大凡零散片断的知识,不但易忘,而且无用。每次所得的新知识必须与旧有的知识联结贯串,这便是说,必须环绕一个中央归聚到一个别系里去,才会生根,才会着花结果。
影象力有它的限度,要把读过的书所形成的知识系统,原来枝叶都放在脑里储藏起,在事实上每每不可能。如果不能储藏,过目即忘,则读亦即是不读。我们必须于脑以外另辟储藏室,把脑所储藏不尽的都移到那里去。这种储藏室在从前是条记,在当代是卡片。
记条记和做卡片有如植物学家采集标本,须分门别类订成目录,采得一件就归入某一门某一类,韶光过久了,采集的东西虽极多,却各有班位,条理井然。这是一个极合乎科学的办法,它不但可以节省脑力,储有用的材料,供将来的须要,还可以增强思想的条理化与系统化。预备做研究事情的人对付记条记做卡片的演习,宜于早下工夫。
《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之一谈读书
朋友:
中学课程很多,你自然没有许多的韶光去读课外书。但是你试抚躬自问:你每天真抽不出一点钟或半点钟的功夫么?如果你每天能抽出半点钟,你每天至少可以读三四页,每月可以读一百页,到了一年也就可以读四五本书了。何况你在假期中每天断不会只能读三四页呢?你能否在课外的读书,不是你有没有韶光的问题,是你有没有决心的问题。
世间有许多人比你忙得多。许多人的学问都是在忙中做成的。美国有一位文学家、科学家和革命家富兰克林,幼时在印刷局里做小工,他的书都是在做工时抽暇读的。
人类学问逐天进步不止,你不努力随着跑,便后进退后,这固不消说,尤其要紧的是养成读书的习气,是在学问中寻出一种兴趣。
你如果没有一种正常嗜好,没有一种在空隙时可以寄托你的心神的东西,将来离开学校去干事,说不定要被恶习气领导。你不瞥见现在许多叉麻雀抽鸦片的官僚们绅商们乃至教员们,不大半由学生出身么?你慢些鄙视他们,临到你来,再看看你的造诣罢!
但是你如果在读书中寻出一种意见意义,你将来抵抗领导的能力比别人定要大些。这种兴趣你现在不能寻出,将来永不会寻出。凡人都越老越麻木,你现在已经不像三五岁的小孩子那样好奇、那样兴味淋漓了。你终年夜一岁,你觉得兴味的锐敏力便须迟缓一分。达尔文在自传里曾经说过,他幼时颇好文学和音乐,壮时由于研究生物学,把文学和音乐都丢开了,到老来他再想拿诗歌来消遣,便寻不出意见意义来了。
兴味要在青年时设法培养,过了正常时节,便会萎谢。比方打网球,你在中学时喜好打,你到老都喜好打。如果你在中学时期错过机会,后来要发展去学比登天还要难十倍。养成读书习气也是这样。
你大概说,你在学校里终日念讲义看教材不便是读书吗?讲义教材着意在均匀发展基本知识。固亦不可不读。但是你如果以为念讲义看教材,便尽读书之能事,便是大错特错。
第一,学校作业门类虽多,而范围究极窄狭。你的天才大概与学校所有作业都不附近,自己在课外研究,去创造自己性之所近的学问。再比方你对付某种作业不感兴趣,这大概并非由于性不附近,只是规定教材不合你的胃口。你如果能自己在课外创造好书本,你对付那种作业的兴趣大概就因而浓厚起来了。
第二,念讲义看教材,免不掉多少拘束,想借此培养兴趣,颇是难事。比方有一本小说,平时自由拿来消遣,以为多么有趣,一旦把它拿来当课一读,用预备考试的方法去读,便不免索然寡味了。兴趣要逍遥清闲地不受拘束地发展,所以为培养读书兴趣起见,该当从读课外书入手。
书是读不尽的,就算读尽也是无用,许多书没有一读的代价。你多读一本没有代价的书,便损失可读一本有代价的书的韶光和精力;以是你须慎加选择。你自己自然不会选择,须去请教于批评家和专门学者。我不能见告你必读的书,我能见告你不必读的书。
许多人曾抱定宗旨不读当代出版的新书。由于许多盛行的新书只是迎合一时社会心理,实在毫无代价,经由时期淘汰而巍然独存的书才有永久性,才值得读一遍两遍以至于无数遍。我不敢劝你完备不读新书,我却希望你特殊把稳这一点,由于当代青年颇有非新书不读的风气。别的事都可以学时髦。我所指不必读的书,不是新书,是谈书的书,是值不得读第二遍的书。
走进一个图书馆,你只管瞥见千卷万卷的纸本子,个中真正能够称为“书”的恐怕还难上十卷百卷。你该当读的只是这十卷百卷的书。在这些书中间,你不但可以得到精确的知识,而且可以于无形中接管大学者治学的精神和方法。这些书才能松动你的心灵,激动你的思考。
其他像“文学大纲”、“科学大纲”以及杂志报章上的书评,实在都不能供你受用。你与其读千卷万卷的诗集,不如读一部《国风》或《古诗十九首》,你与其读千卷万卷谈希腊哲学的书本,不如读一部柏拉图的《空想国》。
关于读书方法,我不能多说,只有两点须在此大抵提起。
第一,凡值得读的书至少须读两遍。第一遍须快读,着眼在理解全篇大旨与特色。第二遍须慢读,须以批评态度衡量书的内容。
第二,读过一本书,须条记纲要和精彩的地方和你自己的见地。条记不仅可以帮助你影象,而且可以逼得你仔细,刺激你思考。
记住这两点,其他琐细方法便用不着说。年夜家资质习气不同,你用哪种方法奏效较大,我用哪种方法奏效较大,不是一概而论的。你自己终久会找出你自己的方法,别人决不能给你一个单方,使你可以“依法炮制”。
作者简介
朱光潜(1897年-1986年),笔名孟实、盟石。中国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教诲家、翻译家。
来源:经济日报微信公号 当代微信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