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提及中国诗词,李白便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
他就仿如中国诗坛上一座光芒万丈的丰碑,永久矗立在那里,一抬眼就会看到。
无论是李白的“蜀道之难难于上上苍”的瑰丽想象,还是“抽刀断水水更流”的哲学思考,更遑论“为君谈笑静胡沙”的豪迈情怀,无不让民气生敬仰。
然而便是这样一个“诗仙”级的人物,却生平屡遭波折,四处碰钉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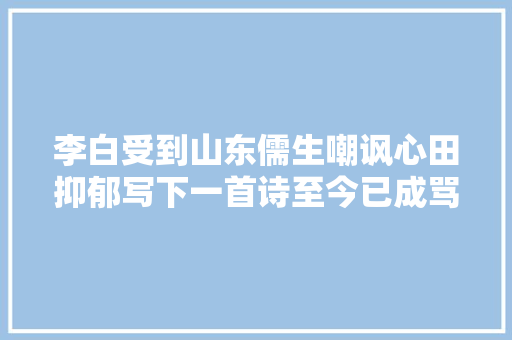
特殊是当他到山东游学时,还受到山东儒生的嘲讽,这让李白感到内心非常烦闷。
于是他大笔一挥写下一首《嘲鲁儒》,这首诗对腐儒的辛辣嘲讽十分到位,至今已成为骂人的绝唱。
一个“嘲”字道尽千年的不屑
公元701年,李白出生在唐朝期间的西域,详细点说便是现在的中亚一带,可以算是外籍人士。
5岁时,他随同做生意的父亲到现在的四川江油生活。
在这里,年轻的李白博采群书,快乐地发展。
当时的蜀地文化是一种复合的、杂交型的文化,词赋、黄老和和筮,历数这才是巴蜀文化的特点”。
于是成长在这里的李白学的就有些杂了,不但“五岁诵六甲、十岁不雅观百家”,而且“十五不雅观奇书,作赋凌相如”。
李白还曾师从纵横家赵蕤,学习其所著的《是非经》。
并且还有多少杂学,诸如“十五学神仙”、“十五好剑术”。
也便是说,总是“十五岁”的李白在攻读文学的同时,还兼修道术和剑术。
当然,作为一个有文化有抱负的青年,他终极的民气抱负是在保持人格的独立和傲岸的根本上,成为一名辅佐君王的士。
如果从今人的角度看,李白便是一个古代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三好学生”。
就这样一贯到25岁时,感到学业有成的李白持着“愿将书剑许明时”的期待,开始由蜀地进入中原,带着一个青年人昂扬躁动的心,游历天下。
李白一起走来一起诗,很快就博得极大的名声,可惜却一贯没有机会实现他的民气抱负。
这时候李白想到了泰山:古代很多人都曾借过“泰山”之力,唐玄宗曾经到泰山封禅,是否自己还有机会等到天子再次光临呢?
于是,在中原辗转多年的李白在736年进入山东。
当然,这时候的李白是抱着“学剑来山东”的想法。
结果未曾料到,他刚刚到东鲁,在汶水之滨就碰着一个老翁。
李白上前问路,表示自己想要学剑学武,未曾想却遭到这个老翁的嘲笑:“举鞭访出息,获笑汶上翁。”
这一下可把李白气得够呛,虽然与老翁辩论一大顿,李白犹不能释怀。
随着在山东待的韶光拖长,见得儒生也越来越多。
李白发现,当时的鲁地有浓厚的周孔遗风、遗俗。
哀求人们的言语行动必须符合“礼”的规范,统统行动必须按照固有的规章制度进行,否则就会被视为歧途。
特殊因此汶上翁为代表的鲁地儒生,他们走的是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入仕之路,两耳不闻窗外事,齐心专心只读圣贤书,思想极其守旧。
可是这次他们碰到的李白却是一个博采百家、思维生动的“杂家”,他的行为举止很多地方都不符合他们认可的“礼”。
鲁地一部分去世守礼节的儒生就认为,李白欠缺“礼”数。
而对付李白来说,他也对一部分鲁地儒生的迂腐和守旧非常反感。
对付他们只会一味地抠词咬字、寻章摘句,却根本没有现实的济世思维和能力大为不屑。
当李白与汶上翁发生辩论,再看到这些人的愚腐行为后,脾气豪迈的他当然会极不认可这些“腐儒”、“俗儒”的作法,于是就有了后世堪称绝响的《嘲鲁儒》。
他将嘲讽的群体定位在岁数偏大的“鲁叟”身上,这首诗第一句就开宗名义:“鲁叟谈五经,白发去世章句”。
他的觉得便是这些岁数极大,一头白发的山东夙儒,只会商《诗》《书》《礼》《易》《春秋》,而且是一贯到老也都局限在五经书里寻章摘句。
然而如果“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
即:当人们想要问问他们经济如何发展,诸如粮食增产、商品发卖等一系列的国计民生,他们就像一头扎在烟雾里一样,什么也不知道。
纵然是这样,他们平日里却是另一副面貌:“足著远游履,首戴方山巾”,纵然每天穿着打扮上却是一丝不苟。
可是他们这种符合“礼”的穿着打扮,却在现实中闹出了极大的笑话:“缓步从直道,未行先起尘。”
意思是他们穿的大袍太长了,一起步就尘土飞扬。
随后李白笔锋一转:“秦家丞相府,不重褒衣人。”
意为:怪不得看重经世济用的秦代丞相李斯不重用这些儒生,实在是太不会变通,学五经都学去世了。
然后李白开始表态,“君非叔孙通,与我本殊伦”。
表明对付这些不懂变通的儒生,与李白不是一起人。
末了一句是最狠的:“时势且未达,归耕汶水滨”。
这就与当代人常说的“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是一个意思。
李白骂人不带一个脏字,却将那些个腐儒、俗儒的守旧固执、不通世事刻画得淋漓尽致,绝对是骂人的千古绝唱。
嘲讽腐儒却尊大儒
当然对付这些在李白心中已经定格的山东儒生,李白险些是见一次骂一次。
后来他又写了“羞作济南生,九十诵古文”,表达出对付儒生皓首穷经式的鄙夷。
他还认为,鲁地儒生过于守旧狭隘,难以容纳贤士。
这时,李白的想象力再次爆发:“鲁国一杯水,难容横海鳞。”
鲁国就像一杯白水那样的小,又怎么可以容纳下能够在大海里横行的大鱼呢?
当然,李白并不是一棍子将山东儒生全部打去世的。
他虽然嘲讽鲁地的腐儒、俗儒,但是对付山东那些能够影响着中华民族精神的文人和知识分子,像孔子、孟子、子思等“大儒”,却绝对是抱有崇敬之意的。
他本人就极敬慕这些“大儒”,而且自谦是“小儒”。
他推崇像叔孙通那样懂得变通,处事灵巧的鲁地儒生,并将自己与其归为一类。
李白能够成为光照千古的墨客,其根本之处就在于他能够兼收并蓄,汲取各地精良的思想文化,博采各家之长。
李白乃至常常在自己的诗歌中,用山东人的典故来抒发自己的情绪,如:“曾参岂是杀人者?谗言三及慈母惊。”
李白也会借用他们的作品内容来丰富自己诗歌的内涵,如:“海鸟知天风,窜身鲁门东。”
鲁地人才辈出,李白除了对山东的思想家有所推崇,对当地的政治家、军事家、侠士的才能与作为亦表示讴歌。
他用“汉求季布鲁朱家,楚逐伍胥去章华”,来惊叹鲁朱家冒死救士的侠士英气和义薄云天的气概。
朱家人身上既有山东游侠的豪士气,又有鲁地文士的儒雅风范,这种品质和风格正是李白所崇尚和神往的。
李白对付东晋期间著名的鲁地书法家王羲之潇洒脱俗的性情,以及清秀俊逸的书法也都给予了极大切实其实定和赞赏,认为他“扫素写道经,笔精妙着迷。”
这解释李白对王羲之其人是比较推崇的。
当然,王羲之身上所呈现出来的豪放洒脱之气,与鲁地人物豪迈豁达的性情是有直接关系的。
李白本人对付山东人的豪迈之气也是极为欣赏的。
西汉期间的名人萧何、曹参、樊哙等都是同刘邦一同起兵的鲁地豪士,李白在诗歌里,对这些人是绝不惜惜赞颂之词的。
李白在东鲁生活了将近二十年,如果他极为反感山东人的话,也不会在那里居住那么久了。
只能说是一部分山东腐儒让李白厌恶,而大多数的山东人却是被李白极为认可并推崇的。
鲁地文化以儒家礼乐文化为核心和灵魂,李白能够在鲁地生活近二十年,恰好可以解释他对鲁地文化的大部分内容是接管的。
腐儒形象在山东只是一小部分,山东儒家思想文化源远流长,在发展的过程中难免有偏离主线的分支,这在任何一种文化传承中都有可能存在。
李白嘲讽的只是那些冥顽不灵、迂腐守旧的儒生,这一类的儒生不但鲁地有,全国各地都有。
只是鲁地是儒家思想文化的发源地,鲁地的知识分子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较其他地方更深罢了。
人们可以看到,在李白的思想中,平等、自由是人们的权利。
乃至是当地一个带着两条鱼一斗酒来看望他的小吏,李白也激情亲切地接待并与之畅饮:“山东豪吏有俊气,手携此物赠远人。”
他想要冲破封建等级秩序的藩篱,以至于他极为推崇平交王侯。
这种追求平等的思想反响在他的诗歌中,便是“府县尽为门下客,王侯皆是平交人。”
然而,这种平等思想与儒家严格的等级制度不雅观念是有冲突的。
李白这种神往自由、追求平等的大墨客,对付儒祖传承下来的森严等级制度和礼仪规范大加排斥和批驳,对付腐儒大加嘲讽也就不足为奇。
对第二故乡的留恋
蜀地是李白的第一故乡,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李白寄居东鲁近二十余年,这一段岁月在李白的生平中也霸占着重要的地位。
他的女儿平阳在鲁地终年夜,儿子伯禽也在鲁地出生。
鲁地是他寄家韶光较长,遗留诗文较多的地方。
因此,鲁地可以说是李白的第二故乡,乃至杜甫、元稹等人都称呼他为“山东李白”。
他也在诗文中用“我家寄东鲁,谁种龟阴田”,来表达自己对东鲁的深厚感情。
而“我家寄在沙丘旁,三年不归空断肠。君行既识伯禽子,应驾小车骑白羊。”以及“桃今与楼齐,我行尚未旋”等诗文,更是透露出李白对鲁地和家人的思念。
这种思念的存在,使外出漫游的李白有了归属感和心灵的寄托。
李白在山东还结交了一批隐士朋友。
徂徕山是齐鲁的玄门圣地,李白时时到此小住,与孔巢父、韩准、裴政、陶沔、张叔明等人酣歌纵饮,时号“竹溪六逸”。
他们相互唱和,留下不少诗篇。
如《送韩准裴政孔巢父还山》—诗中有“峻节凌远松,同衾卧盘石,斧冰漱寒泉,三子同二展”等句,记录了李白等人在竹溪生活的情趣。
而且也是在山东,李白与杜甫两大历史名人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他们二人同游齐鲁,过了一段“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的日子。
在漫游的过程中,他们徜徉山水,诗酒酬唱,留下很多佳作。
杜甫在此期间写出了“李侯有佳句,每每似阴铿。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
让人明显觉得到李杜之间的交情甚笃,亲如弟兄。
并且杜甫在安史之乱时还重温了这段生活,写下“比来海内为长句,汝与山东李白好”的诗句,对李白极为推崇。
在年事上,李白大杜甫十一岁,对杜甫关爱有加。
杜甫对李白也是十分尊敬,两人同游结成了中国诗坛上的一段佳话。
因而山东的部分儒生虽然为李白所厌恶,但是他在山东所得更多。
于是才有李白的“自顾无所用,辞家方未归。”“余既还山寻故巢,君亦归家渡渭桥”等诗句,更是清楚地表明他已经将鲁地当作自己的家园、游子的港湾。
李白生平身怀入仕之志,然而四处奔波,几经挫折,终是无果。
虽然他在仕途中没有什么建树,但历史沧桑,朝代更迭,作为墨客的李白却从未消逝在人们的视野中。
李白是刺目耀眼的,同时也是落寞的,其名虽扬千载,却也枯槁当年。
他在嘲讽那些不通时务的儒生时,实在也是对自己无法达成志向的遗憾。
大概李白的一个判断是精确的,古来贤者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再来一杯美酒,喝醉了再说吧。
文/蓝风烛尘
参考文献:
[1]邱跃坤,李白与鲁郡人的冲突,济宁师专学报,1995(3);
[2]庄梅,李白诗歌与鲁地文化研究,曲阜师范大学,20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