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人生中最要命的便是那场“乌台诗案”,由于一封《湖州谢表》,被政敌有心利用,导致苏轼直接开罪下狱,还连累了一众亲朋好友。
末了,由于有国法“不杀士大夫”,以及王安石和高太后的求情,他得以免除一去世,但活罪难逃,被贬黄州。这次笔墨狱一案,直接导致弟弟苏辙被贬筠州(今江西),苏门四才子也随之消散,然而,受牵连的20多个罪犯中,唯有好友王巩被贬的地方最远且最偏——古人称之为“蛮荒之地”的岭南。
朋友何其无辜受此贬谪,这使苏轼内心十分愧疚,他说:“兹行我累君,乃反得安宅”。元丰四年(1081),苏轼作《次韵和王巩六首》,其一云:
欲结千年实,先摧仲春花。故教穷到骨,要使寿无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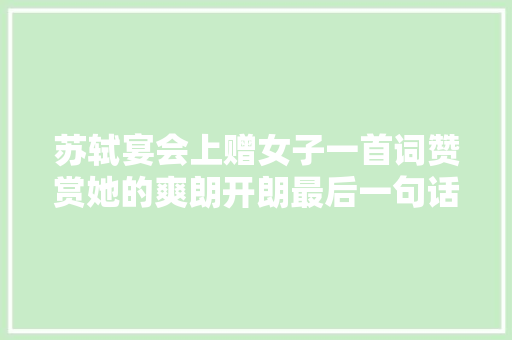
久已逃天网,何而服日华。宾州在何处?为子上栖霞。
王巩在岭南宾州期间,苏轼与他书信往来密切。
岭南瘴气逼人,苏轼担心王巩受不了,建议他用“摩脚心法”对付瘴气,还劝他少饮酒,调节饮食,鼓励他坚持下去,总有一天会枯木逢春。而远他乡的王巩为了安慰苏轼,则给他复书大谈道家永生之术,说自己正在宾州修行。
苏东坡很喜好广西的丹砂等特产,便从黄州致信对朋侪说:“桂砂如弗成贵,致十余两尤佳。”
除此之外,他们还互换诗词书法和绘画心得,并时常谈论国事,互换政见,两名落拓绅士“居庙堂之高而忧其民,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的小儿百姓之心,可见一斑。
由此可见,二人情同伯仲,亲密之情溢于言表。
但对付朋友的愧疚之情,苏轼一贯难以忘怀。后来他给王巩的诗集编序,《王定国诗集叙》中说:
“今定国以余故得罪,贬海上五年,一子去世贬所,一子去世于家,定国亦几病去世。余意其怨我甚,不敢以书相闻。”
公元1083年,王巩奉旨北归,得以宴请苏轼,二人有幸相逢。苏轼创造虽遭此一贬,王巩不但没有平凡谪官那种落拓的边幅,还容颜抖擞,神采愈甚于之前。不由迷惑,“定国坐坡累谪宾州,瘴烟窟里五年,面如红玉”。困境之中,王巩依然豁达爽朗,可见心态非常人所不及。但是,东坡却非常想知道究竟是何缘由使好友如此开明?
王巩笑了笑,不置与否,叫出柔奴为苏轼献歌。只见美人轻抱琵琶半遮面,慢启朱唇,歌声袅袅,分外悦耳。东坡以前也见识过柔奴的才艺,如今也以为她比之前更俏丽了,才艺更精进了,更是迷惑难道宾州水土这样养人么?
于是,苏轼按耐不住自己的好奇心了,试探地问柔奴:“岭南应是不好?”柔奴顺口答以“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苏轼听后,深受冲动,没想到这样一个弱女子竟能脱口说出如此豁达之语,于是对她大为讴歌,急速填词赠她,这首词便是《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使女。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原来,王巩开罪被贬时,家奴歌女纷纭散去,惟有柔奴一人乐意陪伴王巩共赴宾州。这和当日苏轼被贬黄州一样,只有王昭云一人不忍拜别。自古以来,岭南穷山恶水,瘴气横生,柔奴明知此地险恶,却还是乐意和王定国同甘共苦,其心可鉴。
王巩与柔奴二人一起在宾州生活了三年多,两人惺惺相惜。王巩泼墨吟诗,访古问道,柔奴则歌声相伴,温顺抚慰。两人于困境中,相互鼓励,敦促奋发。
只有心情愉悦,才会使人精神抖擞,越变越年轻。因此东坡才会觉得二人红光满面。
据记载,这位柔奴不但琴棋字画样样精通,在音律歌舞方面也有较高的成绩,而且她医术高明,十分同情社会底层弱者,常常亲自上山采药,以其一身医道救治岭南百姓,被岭南公民奉为“神医”。
古往今来,柔奴是唯一一位被誉为女神医的家姬。
柔奴说的那句“此心安处是吾乡”,实在并不是创始,唐代墨客白居易有诗云:“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由此可见柔奴知书达礼,才思敏捷。
自苏轼《定风波》一词传开后,“点酥娘”柔奴的名声便为人所知,而王定国与她的恋情也成为人们口口相传的经典爱情故事。但是,人们更钦佩的如此小女子的豁达爽朗,这对后来苏轼流落儋州时的旷达也做了一种铺垫。
如今,我们再听到“此心安处是吾乡”是不是总有一种莫名的情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