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乐天为中唐绅士,经绅士作名记,沃洲因而形成广泛传播效应,其后慕名而来、而咏者相继而来。
明茅坤《沃洲记》曰:“会稽者,天下之佳山水也。……沃洲又特称为会稽东南之最”,更将沃州山推崇到至高无上的地步。
紧邻沃洲山者为东岇山,二山在历史上相互包含,后来总称沃洲山。山有支遁养马坡、放鹤峰、放马涧、灵澈杖锡泉、水帘洞瀑布等,山旁有沃洲、沃洲湖。山南面有沃洲寺,寺北面为天姥山,寺南对晒台华顶、赤城,北对四明金庭、石鼓。
人杰地灵,人山相得,沃洲早在晋代就已有名遐迩。起初有帛道猷开山居住,其后有竺法潜、支道林等十八高僧相继来居,与王羲之、戴逵、许询等十八绅士在此胜会,一时成为全国佛学中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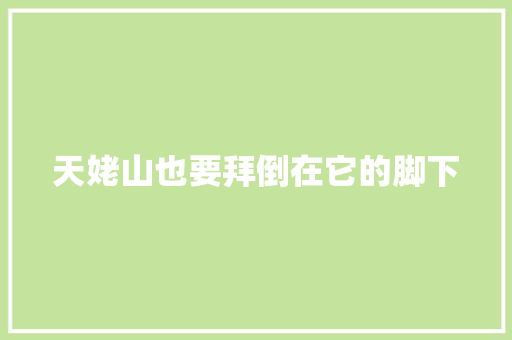
因沃洲方丈僧、即色宗创始人支遁才德高尚,享誉士林,其于此有买山而隐等典故,后来形成“支竺遗风”,流风余韵持久绵长。
据不完备统计,有唐一代来此游历的墨客多达数百,现存诗作近百首,举凡描摹美景、寄托禅佛、抒怀隐逸等志趣,买山而隐、养马放鹤、名流胜会等幽思,不胜列举,精彩纷呈,值得探究。
沃洲,山水秀美,胜景迷人。李白《与南陵常赞府游五松山》:“五松何清幽,胜景美沃洲。”李白自爱名山入剡中,不仅梦游捧红天姥山,对沃洲胜景也影象犹新。
沃洲美景的创造者为鼻祖、东晋高僧帛道猷,其“性率素,好丘壑,一吟一咏,有濠上之风”,隐居沃洲时作有《陵峰采药触兴为诗》,一作《招道壹上人》:“连峰数千里,修林带平津。茅茨隐不见,鸡鸣知有人。……始知百代下,故有上皇民。”
此诗境界开阔,静逸清新,真切动人,乌托邦式的范例环境直逼陶渊明《桃花源记》之武陵胜境,结果真把竺道壹招来共隐。
魏征《宿沃洲山寺》:“一声清磐海边月,十里喷鼻香风涧底松”,境界同等开阔,表现出贞不雅观名臣的豁达心胸。
刘长卿《寄灵一上人初返云门》:“方同沃洲去,不作武陵迷”,言下之意是沃洲山比桃花源还要美。刘长卿在新昌石城有碧涧别墅,写到沃洲的诗歌有十几首。
朱放《剡山夜月》:“月在沃洲山上,人归剡县溪边。漠漠黄花覆水,时时白鹭惊船。”朱放长期隐居剡中,时常往来沃洲。此诗摹绘沃洲月下美景,生动真切。
大历十才子之一的耿湋,曾下江南,游越州,穷山水之胜,留有《登沃洲山》:“沃洲初望海,携手尽时髦。小暑开鹏翼,新蓂长鹭涛。月如芳草远,身比夕阳高。羊祜伤风景,谁云异我曹。”
耿湋在越州时与墨客严维、秦系等相互酬唱。他在沃州山携手一时英杰,登高望远。小暑节气,云开天朗,如大鹏展翅;蓂荚初长,若群鹭起伏。明月似连芳草,夕阳反在身下,极写山之高,望之远。
诗末借用羊祜伤怀岘山贤达不再典故,抒发先贤不可见、美景不常有之悲情。此诗新奇壮阔,是墨客得江山之助的结晶,为十才子中不可多得之佳作。
唐人对沃洲胜景的喜好程度,可用张希复的联句作答:“洲号惟思沃,山名只记匡。”沃洲是惟一,心中是最美,可与匡山(庐山)比较。
沃州山,有水帘洞奇不雅观。只见一派飞瀑,沿山喷薄而下,若珠帘飘垂,不雅观之赏心悦目,引得不少墨客歌咏。如薛能《水帘吟》:“万滴相随万响兼,路尘天产尽旁沾。源从颢气何因绝,派助前溪岂觉添。……嘉名已极终难称,别是风骚不是帘。”
“江东三罗”之一的罗邺《题水帘洞》:“乱泉飞下翠屏中,名共真珠巧缀同。一片长垂今与古,半山遥听水兼风。”
人在洞前,想落天外,二诗极尽形容水帘洞的奇与美。如今,因沃洲上游改造,水源虽有所减少,但水帘依然,仍值得一不雅观。
沃洲,支遁买山,养马放鹤。沃洲洞天福地,自古佛道隐逸之风盛行。魏晋期间,北方战乱频仍,南下中原士族多有隐居剡中、沃洲者,以竺道潜、支遁等十八高僧与王羲之、许询等十八绅士胜会于此最为有名,个中使沃洲山远近有名、古今共识者,非支遁莫属。
言支遁,必言沃洲;言沃洲,必言支遁,二者几成合二为一之关系。因支遁买山而隐,所欲买之山即沃洲山;隐居、方丈沃洲期间,创立佛教即色宗,又有养马、放鹤之举,留下浩瀚逸闻轶事,引人入胜。
支遁,字道林,河南陈留人,一作河南林虑人,东晋高僧兼绅士。才高学富,声动朝野,誉满江东,与竺道潜、王羲之等名僧、绅士往来密切,佳话频传。
支遁向世家大族、琅琊王氏王敦之弟竺道潜(法深)买山典故,出自《世说新语·排调》 :“支道林因人就深公买印(岇)山,深公答曰:‘未闻巢、由买山而隐。’”
而南朝梁慧皎《高僧传》所载更详:“支遁遣使求买岇山之侧沃洲小岭,欲为幽栖之处。潜答曰:‘欲来辄给,岂闻巢、由买山而隐。’”
巢、由隐居深山为避世,买山卖山乃世俗之举,而支遁意欲归隐山林、不惜费钱向竺法深买山,足见对沃州山的钟意与看重。
买山而隐这一不太光彩的本事,却相符唐人高洁、隐逸脾气,故唐诗吟咏者所在多有,并且对这一典故进行深化、拓展,从而衍生出“买峰、买青山、买山钱、道林钱”等典故十几个之多。
如李白《北山独酌寄韦六》:“巢父将许由,未闻买山隐。”仅对买山故事稍作点化,而自然犹如天成。
孟浩然:“支公初求道,深公笑买山。”皎然《哭觉上人》:“忆君南适越,不作买山期。”刘长卿《初到碧涧招明契上人》:“沃洲能共隐,不用道林钱。”
《送方外上人》:“莫买沃洲山,时人已知处。”由此诗可知,到了盛中唐时,沃洲或已名动天下,因来游之人过多,反而不适宜做寂静隐居了。
支公雅癖,养马放鹤。支遁作为一代有道高僧,却在沃洲养马,招来异样眼力。《世说新语》载:“或讥道林养马不韵,答曰:‘贫道但赏其神骏。’”沃洲有养马坡、放马涧、马迹山,皆因支遁养马得名。
另支遁也在沃洲养鹤,怕鹤飞走,就剪断鹤翅。鹤因断翅之后不能高飞而垂头丧气,支遁见之怜惜。
《世说新语》载:“‘既有凌霄之姿,何肯为人作线人近玩!
’养令翮成,置使飞去。”沃洲有放鹤峰,因此得名。唐人咏支遁养马、放鹤佳话者,不乏其人。
有单吟一事者,如孟浩然《宴荣二山池》:“枥嘶支遁马”,贯休《山居诗》:“支公放鹤情相似”。
有养马、放鹤兼咏者,如齐己《道林寓居》:“即问沃洲开士癖,爱禽怜骏意何如。”皎然《支公诗》:“支公养马复养鹤,任性无机多脱略。”
沃洲,佛禅风行。沃州山历来佛缘深厚,晋宋以降绅士高僧于此荟萃,盛、中唐期间更是掀起佛禅之风,沃洲禅诗颇为盛行。
吴越一带绅士僧与墨客绅士,因仰慕晋代支遁、许询、汤惠休、王羲之、谢灵运作诗参禅之风,进而形成一个相对疏松的诗歌群体。
沃洲禅得名,源于曾任越州长史的宋之问《游称心寺》一诗:“自有灵佳寺,何用沃洲禅。”据学者研究,沃洲禅接管领悟了东山禅与洪州禅,更讲求明心见性。
往来剡中的灵一、灵澈、皎然等名僧墨客,既是有道禅师,又是有名墨客,以及晚唐齐己、贯休等僧人僧诗,莫不如是。
感化佛道隐逸之风的绅士墨客,则有刘长卿、秦系、严维、戴叔伦、朱放等。沃洲唐诗,很大一部分与送别寄赠禅僧或僧人作诗干系,在此且举诗僧灵澈与带禅字诗歌以管中窥豹。
禅律互传、名僧兼名墨客的云门高僧灵澈,晚年驻锡沃州山。沃州有杖锡泉,即因灵澈得名。刘长卿、刘禹锡、柳宗元等皆有送别酬赠诗作,如刘长卿《送灵澈上人还越州》:“禅客无心杖锡还,沃洲深处草堂闲。”刘禹锡《敬酬彻公见寄二首·其一》:“悲惨沃洲僧,干瘪柴桑宰。”
柳宗元《韩漳州书报彻上人亡因寄二绝》:“他时若写兰亭会,莫画高僧支道林。”“桂江昼夜流千里,挥泪何时到甬东。”甬东即今新昌沃洲一带。墨客将灵澈比作支道林,可见评价之高,感情之深。
沃洲唐诗带禅字者,如方干《寄江南僧》:“忘机室亦空,禅与沃洲同。”杨衡《山斋独宿赠晏上人》:“何以禅栖客,灰心在沃洲。”鲍溶《送僧择栖游晒台二首·其一》:“师问寄禅何处所,浙东青翠沃洲山。”
以上诸作,沃洲与禅,紧密相连,可证有关学者提出的沃洲禅及诗派其来有自,并非空穴来风,值得重视。
沃洲,绅士胜会。自晋代十八高僧与十八绅士在此雅聚胜会之后,声名远播,堪比庐山白莲社。晋书《王羲之传》与《谢安传》,皆记载二人在会稽与支遁、许询等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雅会情景,可想而知。
沃洲唐诗多有寓意绅士胜会者,如贯休《秋居寄王相公三首·其三》:“只应王与谢,时有沃洲期。”刘禹锡《送僧仲剬东游兼寄呈灵澈上人》:“一旦扬眉望沃州,自言王谢许同游。”
李益《送襄阳李尚书》:“莫废思康乐,诗情满沃洲。”谢灵运酷爱剡中山水,山居始宁别墅期间,常在天姥、沃州、晒台一带巡游、行吟,诗情满溢。
东南山水越为首,沃洲、天姥为眉目。沃州山,山水奇绝,胜景迷人,佛禅风行,绅士胜会,引得唐代墨客纷至沓来,乐不思蜀,称它为浙东唐诗之路的精华之处、点睛之笔,名副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