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洪绶是17世纪上半叶(公元1597年—1652年)的代表性文人画家,因号老莲,明清两代人习气称其为陈老莲。陈洪绶以人物画为主科,在明末的江南画坛上独树一帜。他的人物画追求古拙钝涩之趣,对清代人物画影响极大。晚年的陈洪绶,笔下形象更加变形夸年夜。当代艺术史学者认为,晚明期间,文人画坛涌现了强大的变形主义美学,而陈洪绶是这一潮流的发扬人之一。
在陈洪绶留下的作品中,一轴《斜倚薰笼图》尤其精美典雅。画面的中央形象是一位古装美人,她在一具矮榻上半倚半卧,玉容寂寞。画面在表现什么情节?为什么定名为“斜倚薰笼”?原来,这幅作品是把唐代墨客白居易的一句诗“斜倚薰笼坐到明”转化为绘画。此句出自白居易的名篇《后宫词》:“泪湿罗巾梦不成,夜深前殿按歌声。红颜未老恩先断,斜倚薰笼坐到明。”
诗中的女主角是一位宫妃,曾得到天子宠幸,也曾在宫里风光无限。只管她还很年轻,却很快失落宠,这位失落宠妃子的住处便成了冷宫,终日清清冷冷。残酷的是,新承恩的妃嫔入住的院落并不远,就在前边。于是,前院宫殿里的笙歌声随风阵阵传来,直到深夜仍旧未停。这位失落宠的妃子明知道天子就在不远处,但只能徒然承受着刺激。悲惨的处境让她无法掌握,独自堕泪,又独自用手帕擦干。夜深之后,泪水终于流干了,但她仍难以入睡,又没有办法排解愁闷,只好斜倚薰笼,半坐半卧,熬到天明。
作为当代人,我们可能无法明白,夜里失落眠怎么会倚着薰笼?薰笼又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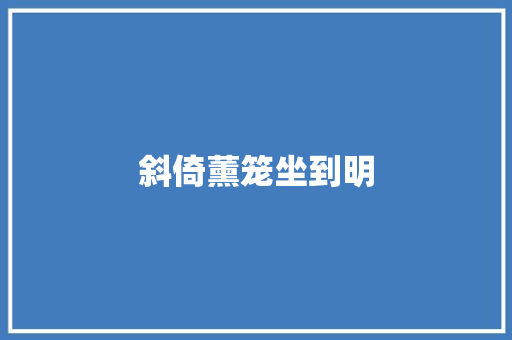
在古代,喷鼻香气是优质生活的基本指标之一,生活的任何一个方面都必须散发“喷鼻香气”。古人也相信,就寝环境丰裕着喷鼻香味,会促进就寝质量,并且让人在寝歇当中调理身心,养生怡神。
于是,在就寝之前特意将被子熏喷鼻香,就成了富朱紫家每晚必须进行的操作。
传统生活特殊讲究用“熏”的方法来使喷鼻香气熏染到丝织物上,日常不仅熏被,更要熏衣、熏手帕。贵族士大夫们的家中都配备成套的专用熏喷鼻香器,由三件套组成,即一只小喷鼻香炉,一只喷鼻香盘(为大盆或者平底盘)以及一只薰笼。薰笼是熏喷鼻香衣被必不可少的物件,其造型大致为由藤条或者竹条编成的一只轻罩,罩面上匀布镂空花纹,供熏喷鼻香的烟外溢。
为追求精细,不同用场和尺寸的织物还要有不同规格的熏喷鼻香专器,以达成最佳效果。熏衣的一样平常为落地式,直接放置在地面上。熏被却是在床上进行,程序大致为:在小喷鼻香炉的喷鼻香灰里埋入烧好的炭饼,再在喷鼻香灰上摆一片隔火片,于隔火片上安一粒喷鼻香丸,让炭火逼着喷鼻香丸缓慢吐喷鼻香。把那喷鼻香烟袅袅的喷鼻香炉立在喷鼻香盘里,然后将喷鼻香盘移至床面的席褥上放稳,扣下薰笼,让喷鼻香盘与喷鼻香炉笼罩在薰笼之中。末了一步,便是以一床被子摊盖在薰笼上,接管喷鼻香烟的悄悄熏洇。
为了熏被,古人用竹条或藤条编出专用薰笼,叫作“床上薰笼”,一样平常为馒头状,整体比较扁平,以便承托被子。在冬季,或者在南方的潮冷日子,把小喷鼻香炉内的炭火烧旺,还能使被子变得温暖和干燥。到了就寝时,把熏被三件套从床面撤走,铺平被子,人们就可以在一袭温暖、芳香的被子下悠然入梦,不必畏惧冰凉与湿润。于是,女性们在期盼心上人来时,会格外留神熏被,务必把一床锦被熏得又喷鼻香又暖。
然而,很多情形都如《后宫词》一样,一个个满含心思的女性徒然将床帐中的卧具细细地浓熏,愿望的人儿却没有来。女子面对漫漫永夜,连撤去薰笼与喷鼻香炉、正式就寝的心情都没有了,便将身体倚靠薰笼上,把被子盖到身上,独守寂寞。
白居易之以是伟大,就在于他能敏锐地捕捉生活的细节,捕捉女性的悲惨时候,并用一句诗凝练地概括出来,让“斜倚薰笼”成为古典诗词里一个隽永的意象。
画家们又把诗句转为画面,让人们从吟咏笔墨转为视觉感想熏染。陈洪绶的《斜倚薰笼图》正是个中的代表作:女主人公寂寞地倚靠在一只竹篾编成的薰笼上,全身都消逝在一条被子之下。薰笼的竹编花纹间可见笼内立有一只鸳鸯造型的小喷鼻香炉,燃喷鼻香个中,熏洇着被褥,也熏洇着美人的周身。
在遭遗忘与冷落的生活中,美人无法排解孤独,只得举头逗鹦鹉解闷。她幼小的儿子不能明白母亲的心情,像统统孩童一样活泼,正玩得高兴,一位婢女在照顾他,把把稳力投放在他身上。偌大的天下,只有一只鹦鹉关注着画中的女主角,与她互动。
此刻,我们感到,白居易诗中的那位宫妃,化成了清楚的形象,展现在我们面前。
在传统社会中, “斜倚薰笼坐到明”并非仅是宫中女性的遭遇,各种背景的女子都可能有同样的凄凉永夜。她或是一位负心人的妻子,或是一位渴望分开苦海的艺妓。以是,在明清时期不雅观众的眼里,《斜倚薰笼图》实在代表了许多被封建礼制束缚的女性,她们无法拥有任何主动性,只能被动地接管命运,斜倚薰笼时,花费的是青春和生命。
白居易那样的大墨客,陈洪绶那样的大画家,虽不能理解造成这些的缘故原由,但仍旧能够敏感地察觉到她们的困境,对她们深表同情,为她们唏嘘惆怅,并用笔墨、画笔,展示她们的痛楚,记录她们的处境,为我们留下主要的历史记录,这不仅是生活史的记录,也是风尚史的记录,更是传统社会下一抹心灵史的记录。而传统社会的男性也很可能在人生的某个时候看到过斜倚薰笼的女性,对那场景是熟习的,一旦读到白乐天的诗句,看到陈洪绶的画,便急速触动影象,产生共鸣。
来源:《环球人物》、《阅读时期》2024年04期
作者:孟晖
编辑:潘茜
【声明:本号为“全民阅读推广”官方公益账号,转载此文是出于通报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缺点或其它欠妥之处,请联系我们。我们将及时更正。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