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家林少华 受访者供图
1987 年 10 月,已经在广州暨南大学日语系任教五年的林少华赴日学习日本古典文学。两个多月后,村落上春树的长篇小说《挪威的森林》问世,全体日本列岛都陷入 \公众 村落上热潮 \"大众。唯有林少华——这位日后的村落上译者一门心思专一于中日古典诗歌研究,对这本摆在书店最显眼处的脱销书熟视无睹。一年后,林少华返国。在日本文学研究会的年会上,他又和这部小说不期而遇——在时任日本现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的李德纯盛情推举下,林少华终于翻开了这本书,没想到读起来便一发不可整顿,很快接管了漓江出版社的翻译约请。\"大众 在暨南大学一个朝北房间的角落里,我就这样陪着《挪威的森林》、陪着村落上春树开始了中国之旅。又眼看着其由不入流的‘地摊’女郎变成陪伴‘小资’或白领们出入星巴克的光鲜亮丽的丽人,进而升格为半经典性天下文学名著。\"大众
迄今为止,包括 2 本与他人合译的短篇集在内,林少华一共翻译了 45 部村落上作品。经由 \"大众 林家铺子 \"大众 加工,作为中译本的村落上作品彷佛多了几分诗意。例如直译应为《听风的歌》的村落上处女作,被林少华意译为《且听风吟》,成为当时文艺青年最爱的社交平台署名,还被朴树写成了歌。在《没有女人的男人们》的译后记中,林少华坦言:\公众 我堪可多少引以为自满的一个小小的贡献,可能便是用汉语重塑了村落上文体,再现了村落上的文体之美。\"大众 面对一些关于 \"大众 译本是否该当完备虔诚于原作者 \公众 的辩论,林少华回应:\"大众 哪怕译得再好再虔诚,百分之百原汁原味的村落上春树也是不可能存在的。\公众
有人称林少华为村落上春树的御用翻译家,他不以为然。在他看来,所谓 \"大众 御用 \公众,是一个天子与臣下的关系,这是不平等的,而译者和作者是平等的关系。除了村落上之外,林少华也翻译过很多日本现当代名家的作品。他尤其喜好翻译与他的文体与心气相通的作家,比如夏目漱石、片山恭一、村落上春树,而对付三岛由纪夫、太宰治乃至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川端康成,则有些违和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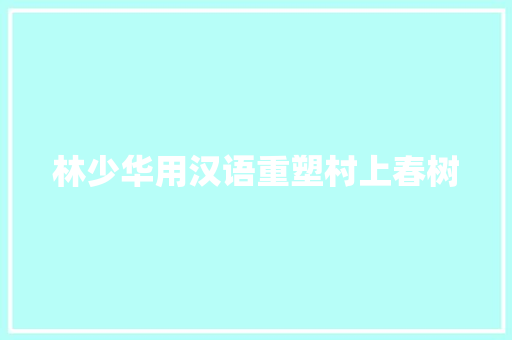
这些年来,林少华开始试着和村落上 \"大众 松绑 \"大众。他开玩笑说,看到自己的名字总是以小一两号的字体跟在其余一个男人名字的后面,有时会以为不是滋味:\"大众 从事翻译,是为他人做衣裳,做久了,就想给自己来上一件。\"大众 他由衷神往回归 \"大众 采菊种豆取水浇园 \"大众 的田园生活,打算据此写一本 \"大众 林氏《瓦尔登湖》\"大众,又捋臂将拳想要写一部 \公众 新《围城》\公众。但问到创作进度,他又谦逊起来:\"大众 小说家的脑袋没准是天生的,而我天生没长小说家的脑袋。去哪儿偷一个回来?这便是当下跃跃欲试的‘进展’。见笑见笑!
\"大众
《挪威的森林》不是普通三角恋
当代快报读品:您最初研究的这天本古典诗歌,《挪威的森林》是您翻译的第一部村落上春树的小说。日本古典诗歌古雅精细,而村落上的文风简洁明快,二者差距很大,当时这部小说详细哪里吸引到了您?
林少华:古典诗歌和村落上小说,当然不是一回事。但作为文体,完备可以共存于一个人身上。如夏目漱石,作为小说家,其和歌(日本古体诗)和汉诗(汉语古体诗)的成绩,完备不输墨客。又如钱锺书,终生从事包括诗歌在内的中外经典研究,但这并不影响他写出《围城》那样的小说名作。作为我,当然不敢和这两位大家比较,但道理是相通的——古诗研究也好,小说翻译也好,都须要诗性。而《挪威的森林》吸引我的,正好是诗性。那是诗性故事,而不是大众文学层面一个普通的三角恋故事。
当代快报读品:翻译家和作家是相互选择的,您认为自己与村落上在哪些方面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
林少华:三点。一是文体上的。我们都追求简约新奇而又不失落蕴藉、富于节奏感的措辞风格;二是代价不雅观上的。我们都方向于同社会盛行的代价不雅观保持间隔,不喜好跟风,不愿意 \"大众 围不雅观 \"大众,甘心自我流放到寂寞的边缘地带;三是审美上的。我很欣赏村落上对不起眼的小景小物小事的审美觉得,尤其欣赏他把无数微茫的感情化作纸上审美的文学追求和艺术修为。
当代快报读品:村落上春树出版了全新短篇小说集《第一人称单数》,不知您是否读过新书了?评价如何?
林少华:原作早就读过了。就觉得而言,不妨说是《神的孩子全舞蹈》《东京奇谭集》《没有女人的男人们》的续篇。水准诚然没有降落,但若要更上一层楼,怕是不太随意马虎了。一来年纪大了,二来谁都有局限性,不可能永久花样翻新、永久一骑绝尘。
翻译并非创作的附庸
当代快报读品:新书《春琴抄》是您的一部译文自选集,个中席卷了不同文风的日本文学名家作品,可以说是您对自己翻译生涯的一次小总结。书名与谷崎润一郎的作品同名,个中有什么深意?有读者解读,认为您因此谷崎书中盲女琴师和仆人的关系,暗喻翻译与您的关系,您是否认同这种说法?
林少华:谈不上有什么深意。自选集一共收了六篇,《春琴抄》是个中一篇。责编问我《春琴抄》和《天皇的帽子》(个中收录的另一篇),书名用哪个好,我说用《春琴抄》吧,毕竟更有有名度。至于那位读者的 \"大众 解读 \"大众,倒是蛮好玩儿的,可我不大认同。彷佛过于自虐了吧——译者的地位怎么会如此凄风苦雨呢?从学科角度来说,翻译学现今已是大公至正的独立学科,博士学位付与权都有了。这意味着,翻译并非创作的附庸。各有各的难度、各有各的代价,各有各的光彩。杨绛师长西席生前倒是有 \公众 一仆二主 \"大众 的说法,说译者像个仆人,一要奉养原著,二要奉养读者,但那属于特定语境中的自我调侃。
当代快报读品:您常常强调翻译时 \"大众 审美虔诚 \"大众 是最主要的,不是笔墨的刻意对应。还曾说过 \"大众 村落上文学的汉语译文已经不再是外国文学意义上或日语语境中的村落上文学,而是作为翻译文学成为中国文学、汉语文学的一个分外组成部分 \公众,是否可以这么说:您认为翻译文本是相对独立于原文本的?
林少华:译作与原作的关系,就文本而言,好比皮毛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但就艺术而言,好比乐谱和演奏者的关系,演奏当然依赖于乐谱,但演奏本身也是一种艺术、一种独立艺术。而且,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只有一个,但演奏起来,效果一人一个样。与此干系,翻译既可以玉成一部原作,相得益彰相映生辉;又可以毁掉一部原作,两败俱伤同归于尽。至于说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一个分外组成部分,这不是我的不雅观点,是已故上外洋国语大学谢天振师长西席最先提出来的,现已得到多数学人的认同。说大略些,毕竟译作因此汉语呈现的,形式上是汉语文本,再高明也和外语文本有差异,不可能百分之百原汁原味。退一步说,就算读原著,又有多少人能读出原汁原味呢?再退一步,文学哪有什么原汁原味呢?越是有误读可能性的,越是精良作品!
当代快报读品:作为日语与汉语文学之间的 \"大众 摆渡人 \"大众,您认为日语与中文表达的相通与相异之处在哪里?若何才能让中文和日文 \"大众 像齿轮一样相互咬合并迁徙改变 \"大众?
林少华:纯粹就翻译来说,我认同周作人的说法:倘日语中没有来自汉语的词汇,可能更好翻译。由于日语中有些汉语词汇同中国原典有奇妙差异,翻译中一欠妥心就会 \"大众 入坑 \"大众,甚至译文每每给人以不伦不类的乖离感。这大概也是汉译日本文学总体上较汉译西方文学逊色的一个先天性缘故原由,可谓先天不敷。但与此同时,作为中国人,作为汉语译者,在体味日文中的汉语词汇方面又有得天独厚的上风,倘有相应的文言文功底和口语文语感,
较之西语译者,理应更能使两种语文 \公众 像齿轮一样相互咬合并迁徙改变 \公众。
方寸之地,无限风光
当代快报读品:您出版了《高墙与鸡蛋》《异域人》《落花之美》等多部散文集,散文中有对自然的亲近和对过往、故乡的怀念,有人情的淳厚,在批驳一些社会征象时又透露着倔强。这些是否都来自从前村落庄生活对您的影响?
林少华:前一部分有影响,它沉淀为故乡情结或乡愁,决定了我的情绪和心灵的优柔部分。而 \"大众 倔强 \"大众 或坚硬的部分,则紧张来自读书、尤其来自小时读的《三国演义》《说岳全传》《水浒传》等旧书,路见不平,拔刀合作!
同时也来自禀性。我天生犟脾气,吃软不吃硬,想活得像条男人,不与小人为伍。见风使舵、见利忘义、鬼鬼祟祟、唯唯诺诺,一向为我所不屑。
当代快报读品:前两年您从高校退休后,操持写一本 \"大众 新《围城》\"大众,这本书的创作契机是什么?目前进展如何?
林少华:在大学(倒不是 \公众 三闾大学 \公众)这个 \"大众 围城 \"大众 里混了三四十年,就这么一退了之,转身拿钓鱼竿或跳广场舞去了,委实心有不甘。于是心想,既然钱先生长西席能以《围城》写出民国教授众生相,我为什么就不能步其后尘,来一本新《围城》写一写共和国教授众生相呢?何况,不是教授的人彷佛都写出《教授》来了,而本人即是教授,焉有写不出来之理!
不过你别说,还真可能写不出来。无他,盖因小说家的脑袋没准是天生的,而我天生没长小说家的脑袋。去哪儿偷一个回来?这便是当下跃跃欲试的 \"大众 进展 \"大众。见笑见笑!
顺便说一句,我还没有实际退休——又被校长另聘为 \"大众 通识教诲讲座教授 \"大众,仍在讲台上摇唇鼓舌喋喋不休。
当代快报读品:您还有一个分歧凡响的习气——每天坚持写微博。最初为什么想要培养这样一个习气?比起正统的文学创作,在微博这样一个碎片化的平台上发声和创作的体验有什么不同?
林少华:最初不是我想写,而是被 \"大众 新浪 \"大众 女孩再三 \"大众 指导 \"大众 的。而我这个人的唯一优点便是有些一根筋,一旦答应人家的事,倘无分外情形,就非咬牙坚持下去不可。不过,微博 140 字也不能完备说是碎片化。谁都知道,唐诗宋词元曲随处颂扬的名篇甚少有超过 140 字的。方寸之地,无限风光。我的做法是,纵然不能表达一种思想、一个不雅观点,也要力争表达一种审美意见意义、一种修辞。说广场启蒙自是不知天高地厚,但客不雅观上多少可能成为连接学术与大众之间的桥梁。一所大学也好,一个知识分子也好,总要有一点文化辐射力嘛!
而被学院派奉为生命线的 C 刊论文,出了校园又有多少人看呢?进一步说来,一天的所思所感盘剥为一则微博,一星期的所感所思发酵成一篇散文或随笔。一两个月的呢,如果恰巧了,有可能涂抹成一篇讲稿或论文。
当代快报读品:您最近在读什么书?有什么可以分享的读书心得吗?
林少华:也是由于今年是木心去世十周年,又看了木心。木心实在是可遇不可求的伟大的 \"大众 布衣 \"大众,关乎文脉,关乎艺术,关乎审美,关乎士子情怀,关乎文化自傲。他的涌现,郁郁乎文哉,飘飘乎仙哉,滔滔乎水哉,崛崛乎山哉,堪称二十世纪人文领域一个奇迹!
只管影响彷佛进步神速,但对他的阅读和研究还远远不足。那是一座富矿,每一锹都可能挖出宝贝来!
林少华
文学翻译家,散文家,学者,中国海洋大学教授。毕业于吉林大学研究生院。曾任教于暨南大学、长崎县立大学,亦曾在东京大学从事学术研究。著有《落花之美》《为了灵魂的自由》《乡愁与良知》《高墙与鸡蛋》《雨夜灯》《异域人》《小孤独》《林少华看村落上:从〈挪威的森林〉到〈刺杀骑士团长〉》。译有《挪威的森林》《海边的卡夫卡》《奇鸟行状录》《刺杀骑士团长》等村落上春树系列作品,以及《心》《我是猫》《罗生门》《雪国》《金阁寺》《在世界中央呼唤爱》等日本名家作品凡九十余部,广为流布,影响深远。2018 年以其精彩的翻译造诣和对中日文化互换的贡献获日本 \公众 外务大臣表彰奖 \"大众。
来源:当代快报全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