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这位作者的举例,作为一个对古代文学有着浓厚兴趣的汉措辞文学专业的学生,我只想一笑了之——凡是对古代文学发展脉络有较为复苏认识的人,都不会用比附古人诗句的方法来说今人所做的诗是抄袭。
可当我浏览下面的评论时,竟有为数不少的人赞赏这位头条创作者“不雅观点雅正”,直呼“说得好”!
这迫使我不得不再去浏览这位创作者所创作的内容,但纵然浏览了两三遍,我还是以为这位创作者分明便是“班门弄斧,贻笑大方”。还是那句话,轻微熟习中国古代文学发展脉络的人,都不会如此大略粗暴的以“抄袭”论郦波师长西席的诗,更不会直呼为“贼”。
可是为什么那么多人都跟风喝采呢?我按耐不住好奇心连续翻看下面的评论,才知道在这位创作者之前,一位名为一凡诗客的创作者早已经由于诗作之事,与郦波教授产生了“争鸣”,并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关注。
02
“争鸣”起源于郦波教授所作的名为《旅夜书怀》(也有版本称《旅夜作书》)的一首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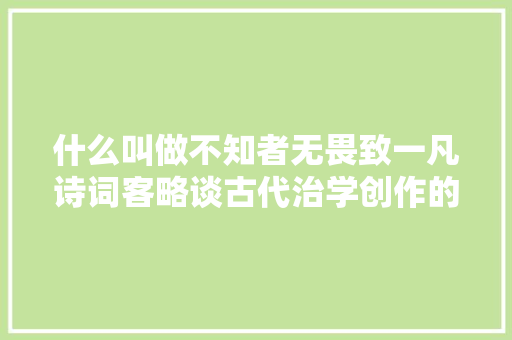
永夜永怀难自问,欲笺尺素赏音稀。
一身多少江湖事,明月清风弄我衣。
一凡诗客自己称,他读了这首诗,如鲠在喉,忍不住要说两句,于是写了一篇名为《改写郦波教授一首七绝兼论名人诗词》的文章。文章字推敲句地评价了郦波教授《旅夜书怀》的优缺陷,并且将这首诗改写为:
永夜奈何凭自问,欲封尺素雁声稀。
推窗检点江湖事,风月满怀尘满衣。
这件事到了这个时候也不过是正常的诗歌互换,创作切磋,可随着后续发展,这件事几次再三升级,一凡诗词客又撰写文章嘲讽郦波教授诗作抄袭。这篇文章出后,为数不少的创作者、“网络评论家”包括笔者在内,都纷纭跟进,揭橥自己的意见。
昨天中午笔者就想撰写一篇名为《今人写不得古诗了吗?浅谈古诗创作中的用典、引用、化用与拼接》来驳斥一凡诗词客的《向郦波教授学习(郦波--从汉唐穿越而来的诗坛妙手)》,可后来创造,郦波教授本人已经就此文章撰写并揭橥了《关于〈旅夜作书〉一诗的详细解答与再回答》,个中列举了大量古人的诗句雄辩地证明中国古代诗歌创作中的引用、化用、用典乃至拼接的传统。
已有珠玉在前,笔者又何必随后抛砖呢?于是,便打消了就此事撰写文章的动机。然而,我本日清晨醒来的时候,溘然又看到了一凡诗词客就此事揭橥的最新文章《感谢郦波教授百忙之中的回文》。读完这篇文章后,我心中一笑,想起了他在先前文章中的所言:
本人狂悖,冒然改写郦波教授的大作。幸得郦波教授专门发文回答精解并劝我多读多练。苦读之后,真正觉得到自己的孤陋寡闻。
他明明知道,自己孤陋寡闻,随后却仍旧大言不惭地试图用数据来驳斥郦波教授。看到这里,我心中暗自大服一凡诗词客不愧是高等司帐师,什么事都懂得用数据来说话,乃至还精确到了小数点后两位。他在文章中说:
1. 曹孟德的“青青子衿,悠悠我心”8个字,占《短歌行》128字的6.25%
2. 王勃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14个字,占《滕王阁序》971字的1.44%
3. 李太白的“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占《行路难》95字的14.73%
后面16个例子就不赘述了,再说了郦教授也没有把化用的、整句借用的例子分开列示。我也扒拉不明白,就按字数统计吧。
如果按照他的逻辑,他的算法,上面的例句中所算的数据该当不差。但是抄袭怎么能够这样来算呢?就单摘出来一篇诗文中的一两句这样算的重复率当然很低,可是如果把曹操《短歌行》、王勃《滕王阁序》和李白《行路难》等诗文中所有用典的句子,都进行查重,其他人不说,王勃铁定无疑要带上“抄袭”的帽子。
正如郦波教授在其文章下方评论中所回答的:
汉语与中国诗学的特点,导致了古诗词创作中经典语词与组合办法的重复性、相似性。这一点越今后期越明显,以是小学兴盛,一是探寻“主旨”,一是考寻“来处”。但并不能只凭语词相似来定“来处”。不相信您来一首,我可以按您的标准找出句句“抄袭”之处。
实在,不但是诗歌,通读了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史,我们很随意马虎就会创造,中国古代所有的文学作品都讲究“继续性”,讲究“有史可稽”、“有案可查”。
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虽然古代传说是由孔役夫删定的,但他的创作和流传绝非出于一时一地一人之手。个中的雷同的句式、字词俯拾皆是,如果按照一凡诗词客等人的逻辑,恐怕这也算抄袭吧?那他为什么不去挑《诗经》的毛病,而单单揪住郦波教授一个人的一首诗不放呢?由于他自己也知道,他去挑《诗经》,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除诗歌之外,我们再来说一说散文、小说和戏剧(戏曲和杂剧)毕竟文学有四大文体,诗歌只是个中的一类。
先来说散文,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散文莫过于“唐宋八大家”的散文,如果用现在的查重软件来查他们文章的原创度,其他的我不好说,但笔者可以肯定的是,韩愈的大部分散文以及该当都是过不了原创的。至于魏晋六朝、乃至上文提到的王勃、没有提到的杜牧等人的骈文,其原创程度更是堪忧。当然,我是一个文科生,不善于拿数据说话,如果一凡诗词客有兴趣,不妨去查一查,算一算。不过我要提醒其把稳的是,要综不雅观全文,逐字核查,这样才能得出全面的数据。
其余说说小说,轻微爱好文学有点文学知识的人,都知道中国古典小说有四大名著:《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实在,除了这4部之外,还该当加上一部《金瓶梅》和一部《聊斋志异》这是我心中的古典小说六大奇书。
就《三国演义》来说,人所共知,这部小说紧张脱胎于西晋史学家陈寿撰写的《三国志》,不知一凡诗词客在阅读《三国演义》的时候有没有如鲠在喉的体验?
要知道,《三国演义有》很多都是原封不动地照抄《三国志》原文。
再来说戏曲,《西厢记》纵然大家没有阅读原著,也都该当听说过,个中故事最初源于唐代大墨客元稹的《莺莺传》,后经历代演化终极由王实甫写成了《西厢记》,此间几百年有诸多不同的版本问世,其情节故事,乃至遣词造句不是说大有雷同,便是千篇一律,恐怕任何一个学习过古代文学的人都不会说他们是相互抄袭。
一言以蔽之,这是古代文学的特性。以是,“天下文章一大抄”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广而言之,不但是文学,中国古代所有的学问都有这样的“沿袭继续性”。
以史学论,《资治通鉴》是全球皆知的伟大史学著作,但是个中大部分篇章,尤其是隋唐五代以前的都是从各种史籍中抄录而来的,原模原样,一字不变的篇章有的是。不过,我想千年以来除了无知无畏的跳梁小丑,该当不会有谁公然的责怪司马光抄袭,说他做贼,最多说史料代价不高,原文摘录而已。
根据我多年阅读、写作的履历,想要在诗歌领域乃至在全体文学领域乃至全体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想要有独立的创见,真的很难,如果翻用古人之意,古人之句都是抄袭做贼,那文科生没法活了!
由此推而广之,一凡诗词客已经不是向郦波教授开炮,而是在向全体社会人文科学领域的学子、学者开炮,大概是由于他是学司帐、搞数据的吧——站着说话不腰疼!
古人能够原句原文的引用,为什么今人就不能?为什么别人可以翻用古人的诗句,乃至是引用成句,郦波教授就不能呢?还是有人真的是无知无畏,故意寻衅滋事呢?或者说,归根结底,还是曹丕说的那句: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呢?
写到这里,我想到了吴敬梓的《儒林外传》,我昨天就成写道:如果吴敬梓现在还活着,恐怕可以续编一部《儒林外史》了。然其人自知不在儒林之内,而又在儒林之外乎?末了,我又想到了唐代文学家杜牧的一句名言,这里略微改动,作为全篇结尾:
其人不暇自羞,而旁人羞之,旁人羞之而不鉴之,亦使旁人复羞旁人也。